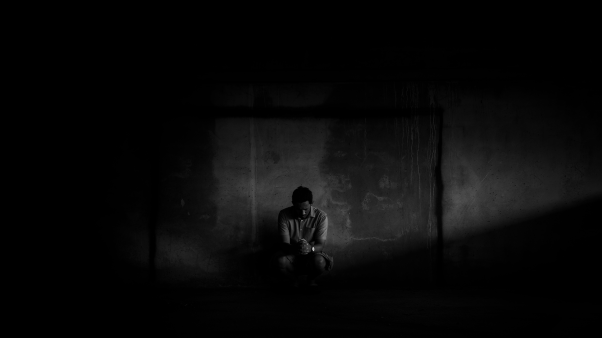近期,美国有不少基督徒将注意力和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转向初代教会对于单身和与性相关议题的教导。许多讨论集中在关于历史上的独身主义及属灵操练,和早期教会领袖对单身的教导。
有些人认为,早期教会领袖积极地“拆毁”婚姻在教会里的核心地位。其他人则认为,我们今天对(所谓的)“独身的恩赐”的理解直接承传自使徒和初代教会。
身为一个历史迷、实用神学家和尚未结过婚的基督徒,我可能无法同意以上任一种假设,但我很高兴看到关于我们应如何从新的角度看待初代教会单身观念的讨论得以复苏。毕竟,教会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那个古老的时代充满关于单身议题不少有趣的见解(以及相当多的难题)——其中有许多议题仍与今日我们对信仰和教会生活的探讨息息相关。
关于单身的教导,我们可以从早期教会学到极多且重要的想法,但它们既不简单也不好懂。事实上,早期教会领袖们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单身生活的单一种论述。然而,当我们单独考究基督教独身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我们的对话会涵盖不少复杂又有趣的内容。
那么,当我们忠实地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首先,正当的历史研究法涉及观察过去种种细节和细微的差别,而不是粗略地一笔带过。
我们必须牢记,初代教会时期跨越了近500多年和几个不同大陆。在那个时代和空间里,对尚未结婚的单身基督徒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不少的共识,但也有强烈的分歧。
例如,回顾一下第四世纪的教会是如何回应曾是修道士的乔维尼安(Jovinian):只因他勇敢提出“处女、寡妇和已婚妇女,只要接受过基督的洗礼…… 就有同等的地位”这种不考虑基督徒的婚姻状况,直接肯定他们在基督里同享平等地位的想法,最终导致乔维尼安一生在多个宗教会议里被判定为异端。
这样的论述还激发了教父们大量且长篇的论述,如早期教父耶柔米(Jerome)(他疾呼,“如果读者被迫阅读乔维尼安写的恶心垃圾,不要因此感到不安”),甚至是奥古斯丁(他感谢教会“非常一致且有力地反对这个邪恶的人”,同时“用主赋予我的所有力量”阻止乔维尼安“秘密地㪚播毒素”)。
或者我们能想想,在帝国东部地区的未婚基督徒的生活的特征,与西部地区的完全不同。约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期,两个地区对于基督徒的单身生活皆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神学论述和实践方式。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初代教会对我们现今所谓的“单身的议题”的理解很复杂,并没有简单或单ㄧ的观点。
第二,若想探索过去,必需坚定不移的去理解历史的动态性。
近期,“独身主义”一词在福音派圈内热门起来,但现代的讨论往往将独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终生的、或正式地对某种特定单身型式所作的承诺及委身。
一些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认为独身主义直接继承于古早历史里的一种属灵操练。然而,在其最初的记载中,celibat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caelebs,这个词单纯意指“未婚”—— 与我们如今的“单身”一词有异曲同工之意。
更重要的是,在修道院的模式成型以前(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独身主义时通常会想到的群体),有各式各样的未婚人士,包括巡回教师、独居沙漠的隐士、苦行派的成员、独身神职人员、一般的处女、寡妇和鳏夫等等。
在教会初期的年代,未婚基督徒所呈现的生活样式不仅更加多元,而且其中一些还被认为是神学上有问题的。
以禁戒派(Encartites)为例,这是在第二世纪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他们强调以不吃肉、不喝酒,或最重要的排斥性行为来作自我约束的操练。禁戒派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他们“完全拒绝婚姻”。
这个运动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但到了第三世纪初,初代教会教父如爱任纽(Irenaeus)和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积极反对禁戒派。他们认为,禁止婚姻(以及婚姻中的性行为)是异端邪说。正如大卫·亨特(David Hunter)在他的《古代基督教中的婚姻、独身与异端》(Marriage, Celibacy, and Heresy in Ancient Christianity)一书中所指出,“此时期的‘正统’的基督教意味着接受婚姻和摒弃激进的禁欲主义”。
无论这情况对我们这些现代的历史读者带来多大的不便,但初代教会里完全没有明确的“独身生活”的定义,或单一的实践方式。
第三,与过去打交道需谨慎地注意历史的连续和不连续性。
我们必须认知到,现今的“单身生活”在文化背景上与初代教会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比如,今天的单身基督徒在决定为何结婚、与谁结婚、何时结婚方面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权。这种婚姻的独立性对古代的基督徒而言是无法想像的。对他们来说,婚姻基本上是社会结构的一部份,以及经济上的必要存在——往往由他们的长辈或家人作主,无论他们喜欢这种安排与否。事实上,在最早的几个世纪里,多数未婚的基督徒并非”从未结过婚””的成年处女或处男,而是丧偶的丈夫或妻子。换句话说,长期的独身状态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曾有过一段婚姻之后!
即使当更委身的独身操练开始发展了,选择委身于这样的生活形式也被视为一种稀有的奢望,有时甚至是自我的放纵。这种特权一般只有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菁英才可享有,因为他们有能力违背家庭的期望。
虽然我们可能会想画一条线把现代和过去的单身生活形式连结起来,但历史上的不连续性远远超过连续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经验不能为现代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
但这也确实表明,今天的基督徒们努力想解决的许多问题与古代信徒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身为负责任的历史读者,我们必须很愼重,不要傲慢地把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强加于过去的方式之上。
最后,“挖掘过去的历史”这行为本身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对自己的动机诚实。
当我们今天谈论著基督徒的单身问题时,我们必须坦诚——对我们自己以及对别人——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想利用类似的历史例证来支持我们已有的信念吗?
在《修正性的神学》(Theology as Retrieval)一书中,作者大卫·布斯查特(David Buschart)和肯特·艾勒斯(Kent Eilers)称这种错误的动机为“内线防御工事(retrenchment)”。这种策略的目的是希望能巩固我们已经挖好的战壕,并把我们的双脚和旗帜牢牢地插在里面。
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对今日教会面对单身议题的方式感到极度失望,以至于想把一切都抹煞掉,从新开始?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一成不变地接受过去的方式?这是布斯查特和艾勒斯所说的死灰复燃——用美好的眼光怀旧地看待过去的一切。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不该利用历史来巩固已有的立场,也不该一成不变地承继过去——那么历史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尤其是当我们思考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社群内的单身议题时?
那趋动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前辈是如何思考一个未婚基督徒与神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动机,应该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回归本源(ressourcement)——也就是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应定意致力于根据它的历史上下文来真正的理解它。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丰富的资产,以便在今日增加我们对单身生活的理解、能去活出并赞颂单身的状态。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方式也强调一种委身的态度,即完全按照另一种标准来积极地审视教会历史——但不是按照任何人的标准,而是基于上帝自己透过《圣经》所启示的标准。
历史上修道院的独身做法也许与我们对于如何在今天的社会里“作”单身的基督徒有某种呼应。事实上,许多初代教父在他们的著作里高抬单身的价值,在我们今天看来那是多么地美妙(以及陌生!)。
但是,在我们能感激过去的经验以作为今日的资源前,我们必须先下工夫读《圣经》。当我们在思考是否接受某种结论,或应用过去历史里的属灵原则时,我们必须将每个观点放在神话语的亮光下检视。
首先,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即基督的肢体在我们所属的教会群体内的展现,是我们属灵家庭身份的主要来源(哥林多前书12:12)。同样地,我们反对任何对历史粗暴的解释,认为初代基督徒完全拒绝婚姻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并没有)。
最后,我们必须努力了解初代基督徒是如何及为何会有他们当时持有的想法——他们的结论是否有《圣经》的依据。
在现代许多关于“单身的恩赐”(林前7:7)的解经中,有些人会用“向来如此”来为某段经文的单一解释作辩护。但是,若我们真诚地把历史当作重要的资源时,我们必须确认它是否确实一直只有这种解释方式。
而每当谈及“单身的恩赐”时,教会历史里往往没有单一的标准答案。即使假设当年真有一个标准答案,现今的我们仍需用神的话语去检验,以确定古代和现代读者的解释都没有偏差。
身为历史学家,我们知道历史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然而身为基督徒,我们最终只有一样无价的资源(圣经)。归根结底,只有透过经文的检视及倚靠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明辨出教会在单身议题上的历史进程,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为何以及是如何的重要。
丹妮尔·特维克(Danielle Treweek)是一位神学作家、讲员,也是“一心一意”(Single Minded)组织的创始董事。她关于单身的博士研究将于2022年由InterVarsity出版。
翻译:江山 / 编辑: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