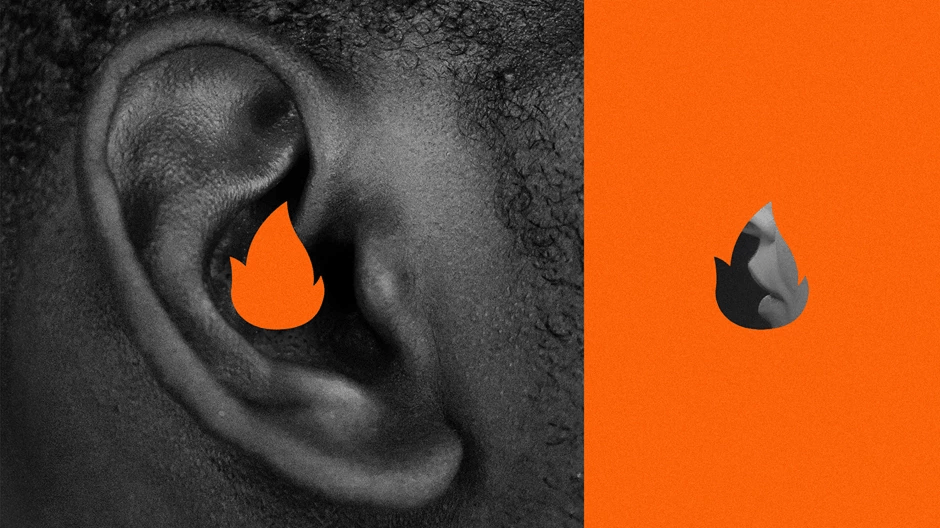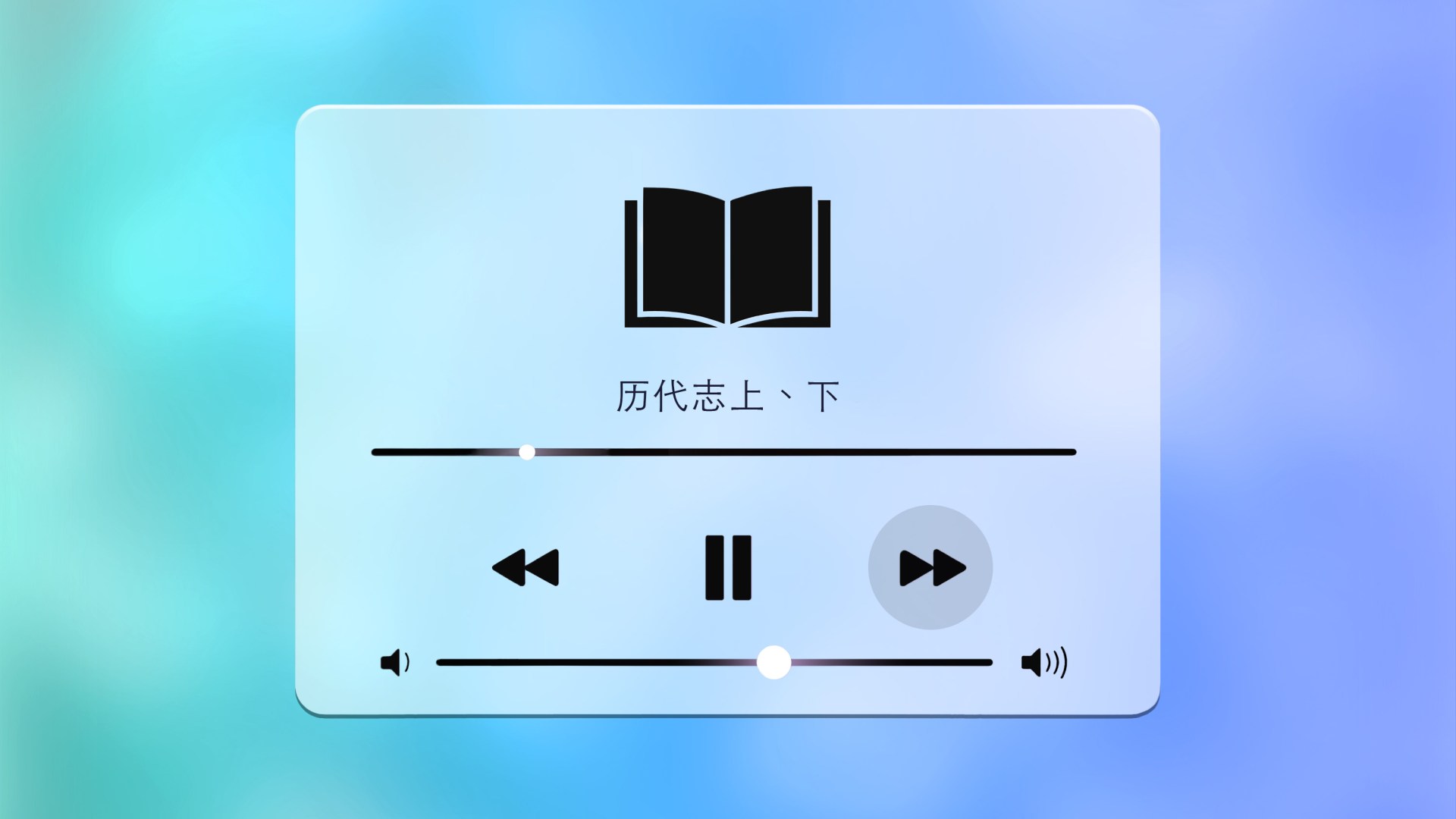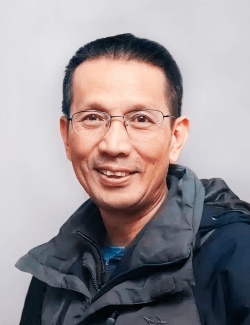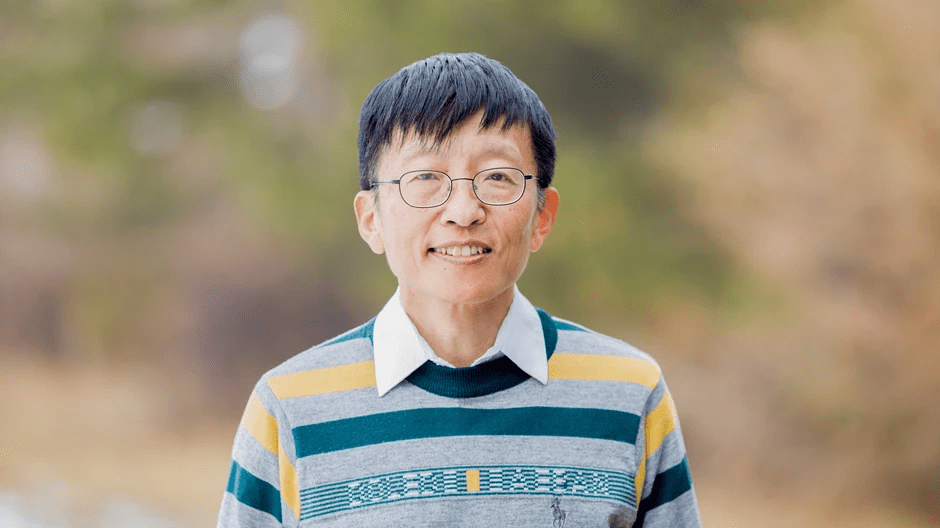如火一般的舌头,无所不在。在这个喧闹和愤怒的时代,在这个抗议及反抗议的时代,言语燃烧、灼烧、烫伤、刺痛着人们。
雅各曾写道:“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但是,我们很少人——即使是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愿意相信这句劝言。我们不相信“多听少说”于我们今日面对的现实有益。
正如迈克尔·威尔(Michael Wear)在《我们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Our Politic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屈服于相信“在这个时代需要用敌人的工具(来打败敌人)”的诱惑。我们为自己的火舌辩解,认为“这只是加入你玩游戏的方式”,却无视我们造成的破坏痕迹——我们嘴唇上的火花毁掉了大片森林(雅各书3:5-8)。
当然,太阳底下无新事。愤怒以千兆赫的速度传播,比信使传播得更快,但我们的时代并非独一无二混乱或动荡的时代。教会经历过更糟糕的情况,尤其是基督复活升天后最动荡危险的初期。
“我被关进监狱⋯⋯挨打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我被犹太人用三十九根鞭子抽了五次,被罗马人的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砸了一次。⋯⋯我不得不越过河流,抵御强盗,与朋友搏斗,与敌人搏斗,”使徒保罗讲述着他在那个时代的传道经历(林后11:23-27,MSG信息版)。
这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圣灵临到门徒时的文化处境。圣灵向世界释放另一种火热的舌头——它带来连结、启迪灵魂和清晰的见解,而不是分裂、破坏和混乱。这就是我们在五旬节主日纪念并庆祝的属灵产业。我们需要重新抓紧这份产业,因为我们的时代同样需要这些火舌,以及伴随而来的相互理解的奇迹。
在我加入其青少契的那间教会里,任何关于“一阵大风”吹进门徒聚集的房间的讨论,都集中在这类或那类的方言上(徒2:2)。在灵恩派青少契里,教会长老们(—深信圣灵的第二次祝福或第二次洗礼)和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会说其中一种祷告语言(或称方言),就不能在青少契领袖小组里服事。(所以我没有)
同时,我在主日早上参与的另一间明显不属于灵恩派的教会基本上不会提及圣灵。这间教会将“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变成古老的美好回忆,将圣灵的显现看作类似博物馆的展览——饶富文艺复兴风格的艺术品在人们平静、圣洁的头顶上舞动着娇艳的火焰。也许在初代教会发生的事有点奇怪,但我们的教会井然有序,一切合乎常理,正常且可预见。(这间教会的解读确实抚慰了我的自尊心,让我确信自己的灵命并不比青少契的同侪差)。
尽管这两间教会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他们试图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五旬节的“舌头神迹”?这个问题的焦点非常单一,以至于我直到成年后才知道五旬节还有第二个神迹:除了舌头的神迹,还有耳朵的神迹。
在这个被巴别塔的混乱所困扰的世界里,上帝派遣祂的圣灵来恢复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能力。五旬节主日既标志着说的神迹,也标志着聆听的神迹。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却没有人在聆听,我们对雅各书所形容的那种火舌的了解远远多于使徒行传里医治的舌头——五旬节那日,人们彼此互惠的奇迹正是这个焦灼的世界需要“我们的教会”再次体现给世人看的。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领袖智慧小书《狼要与羔羊同居》(The Wolf Shall Dwell with the Lamb)中,美籍华人圣公会牧师艾瑞克·罗(Eric H. F. Law)以当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动态作为呈现使徒行传第2章的框架,以此来解读所谓的“沟通的奇迹”。
艾瑞克牧师写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两群人聚集在一起。首先是门徒,他们大多是来自加利利的渔夫和工人(我们今日可能会说他们是带着乡下口音的乡巴佬或大老粗)。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后面所了解到的,彼得和约翰等初代基督教领袖在犹太长老和文士眼中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在罗马殖民者眼中,他们“只不过是犹太教的另一个教派,该教派领袖已被处死”。
第二群人是“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徒2:5)。相较于门徒,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是犹太菁英。有些人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花费不斐。或许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撒都该人,是宗教贵族,在犹太公会中占有席位,具有政治影响力,并与罗马政府的权贵有联系。就在几周前,有些人可能还参与了要求彼拉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行动。
艾瑞克牧师认为,简而言之,第二类人可能会为耶稣的跟随者带来麻烦,或什至其中一些人已经带来了麻烦。然而,圣灵正是给了这群人“聆听并理解的恩赐,尽管门徒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人群中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恩赐——有些人还以为门徒喝醉了——但许多人确实听懂了,并对他们所听到的感到惊讶(徒2:5-13。
在圣灵降临节上,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并带来了“公义、圣洁和救赎”(林前1:27-30)。软弱、无知、无能的人被强大、受过教育、有权势的人所理解了。基督颠倒的国度颠覆了世界的常规。圣灵的火舌带来的是光照,而不是伤害。
今日的我们——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这样的故事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强而有力的那一方,还是无能无力的那一方?这个问题因个人种族、教育和阶级等因素而变得复杂,却是我们许多场文化战争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同样的行为和恐惧,如果是来自受困的少数群体,而不是偏执的多数群体,其表现形式就会截然不同。
我自己的背景是白人、农村和工人阶级。如今,我和丈夫都是稳固的中产阶级,但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而且我是勉强摸索着才考上大学,因为我不了解SAT考试对入学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报名参加。我的家乡不是加利利,但可以算是美国版本的加利利。
我认识并深爱着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在日渐凋零的小镇上艰难度日,试图想像自己的孩子在空洞化的社区里会有怎样的未来。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拥有特权或有什么权力地位,都对被人认为是特权阶层而感到不满。根据不同的新闻立场,这群人——我的村民——要么是一群受害者、因被遗忘而合理地充满怨恨的族群,要么就是无知的傀儡法西斯分子,对美国民主构成生存威胁。
这两种对立的形容词某种程度上来自沟通不良的问题。我们喋喋不休,却不愿倾听,因此我们无法互相理解,甚至在教会内部也是如此。我们说出别人的罪,却对自己的罪保持沉默(马太福音7:3)。我们忽略其他人所处的群体与我们的群体之间复杂又细微的差异,我们以苦毒还苦毒,加入铿锵的敲锣打鼓演奏团(林前 13:1)。
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教会需要来自圣灵的清新之风。我们必须悔改,悔改我们正在以所有方式成为一个“惧怕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力量”远胜过“惧怕上帝的力量”的教会。我们必须祈求上帝透过圣灵帮助我们寻求在五旬节那日发生的两种神迹。
这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无论我们更倾向视自己为加利利人还是所谓的“更有智慧”的听众,都是如此。我想,同时在这两类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的不会只有我:在某些情况下,我的肤色或说话的内容给了我相当大的优势;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我是一个乡巴佬,不知道如何在权力的殿堂自处。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我的身分由祂来定义,我愿谦卑地顺服基督的呼召——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腓2:3)。在所有情况下,我都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一切所需。
我想,对耶稣所有的跟随者而言都是如此。有时,我们需要舌头/言语的恩赐:这种决心让我们有能力站在该站出来的地方,抵制必须抵制的事,说出该说的话。但有时我们需要有耳可听见的恩赐,因为上帝要求我们安静下来,倾听,并驯服我们的舌头。
有时我们有很多权力、力量。有时我们没有;有时我们有很多需求,有时我们则很富足;有时我们会享有特权,受人尊敬,有时我们被人谩骂和蔑视;有时我们需要捍卫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有时我们需要为人舍己。但在所有人生季节里,我们都有圣灵的陪伴,祂总是热切地在我们里面做工,并透过我们的生命产生上帝想见到的那种公义。
Carrie McKean是一位居住在西德州的作家,她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得克萨斯月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