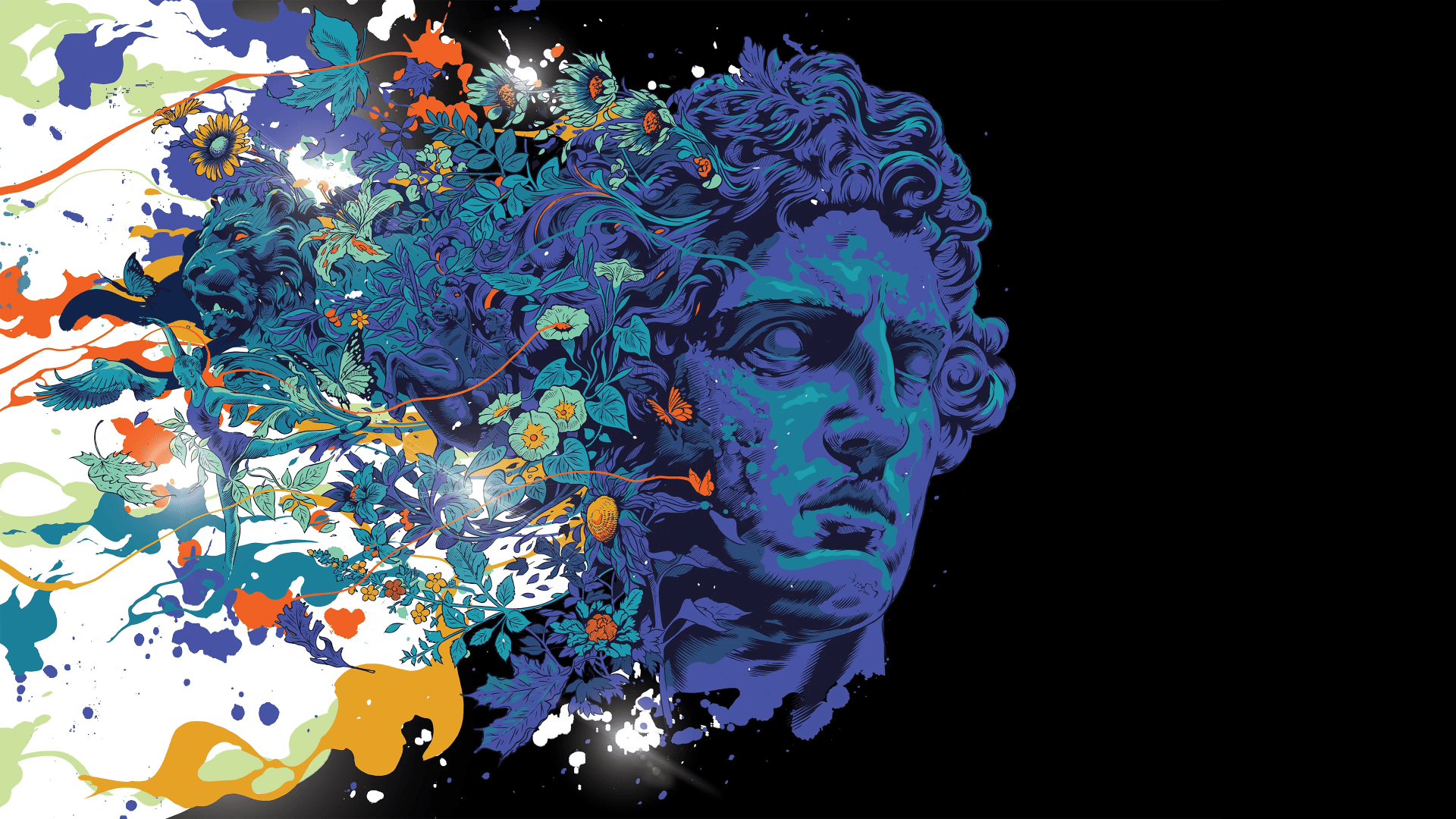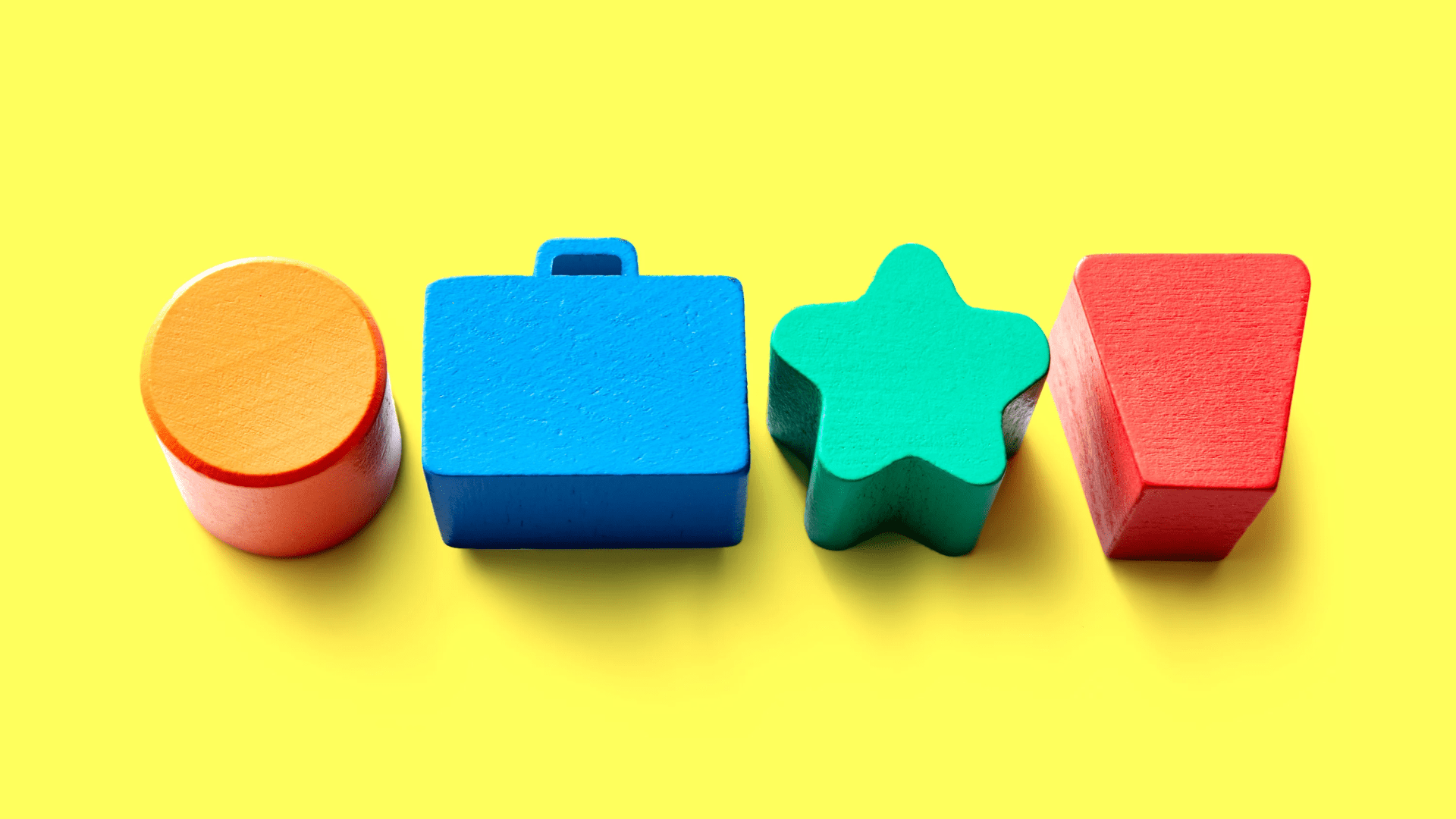任何想把全世界一亿多个说华语的基督徒连结在一起的人,都必须处理中国教会这个棘手的问题。在中国,基督徒分成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和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注册教会)。此外,政治观点上的激烈分歧使得全球华语教会难以合一。
尽管如此,全球福音派领袖仍希望将华人基督徒团结起来。上周,世界福音联盟(WEA)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TSPM)和中华基督教协会(CCC)的领袖会面(这两个组织都由中国共产党监督),并向他们发出合作的邀请。
WEA于一年前成立世界华人基督教联盟(以下简称WCA),以智库、出版社、媒体中心、学术交流、资源分享和训练等方式服事华语教会。
WCA及新加坡WEA总干事Ezekiel Tan接受本刊的采访,谈论WCA的宗旨、目前的进展,以及将世界各地的华人集结在一起将面临的独特挑战。
WCA是WEA第一个以语言为基础建构的基督徒关系网路,而非WEA典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网路。为什么WCA选择以中文普通话作为此种尝试的先驱?
中文普通话是我们的第一个尝试,因为中文使用者很独特:他们多数具有汉族基因,祖先之ㄧ曾来自中国(地理地区)。其他国际语言群体,例如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则包括来自不同种族的人。
由于华人人口如此分散,只要接触到华人,你几乎能接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唯一的差别是有些人读写简体中文,有些人读写繁体中文。当你用中文生产一些东西时,会有一定规模的经济。
然而,“房间里的大象”是围绕着中国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很多时候,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会互相猜疑。我们不希望其他团体歪曲理解基督教群体,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
华人也具备不少财力资源。在许多亚洲国家,华人虽然是少数群体,却管理着不成比例的财富和资源。接触华人不仅能帮助我们改善社区之间的资源分享,也能促进全球运动中更大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捐赠。
WCA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平台,但这个平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构在现有的全球性网路上,例如在189个国家训练基督徒领袖的哈该国际(Haggai International),或是各国的圣经学会。
WCA是华人事工及外展的全球平台。它将所有华人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分享中文的基督教资源,例如主日学教材、中文敬拜歌曲,以及与全球华人教会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并提高他们各自工作的效率。最终,我们盼望WCA能帮助我们完成大使命。
WCA的目标不是什么?
秉承WEA的主要精神,WCA不是政治性的,我们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中立的平台,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将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此外,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有华人基督教机构的全球管理机构。 WCA是个让现有机构和组织互相交流的平台。我们不是要与任何现有的网路竞争。相反的,我们希望扮演一个补充的角色。
因此,我们邀请任何已致力于某项中文事工的机构加入我们。 WCA并非以地区为中心。虽然我们向华人传福音,但这并不表示亚洲是主要的基地。我们寻求以全球为中心,而非以地区为中心。
WCA 于去年七月正式成立。它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目前,我们专注于WCA的基础建设,预计还需一年时间。媒体中心仍在起步阶段,我们一直在与各方沟通。在资源分享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也出版了一些书籍。
培训中心是目前发展得最好的项目。在项目开始前,我们已举办过培训,每年有来自20个国家约二至三万人参与我们的培训。我们会在不同国家寻找知名的华人讲员,就我们认为有帮助的主题做演讲,例如亲职教育、沟通或圣经阐释。我们透过关系网络宣传我们的训练项目,邀请人们参加。
第二个层面是要触及全球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包括非洲、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的教会领袖。虽然我们的预算有限,但已有许多讨论和访问。
第三层面是我们如何与中国互动的问题。很明显地,绝大多数的“华人”正住在中国。在最近ㄧ次访问前,我们曾多次拜访不同国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各地政府。然而,在中国,我们需要以非常官方及正式的方式做事,所以上周,由WEA国际理事会及其地区领袖代表组成的官方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三自教会的领袖重新建立关系。
在这次旅程前,WEA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次访问之后,再也没有跟进任何更有意义的互动关系。这次的拜访具有突破性,因为它标志着一个长期关系的开始。
我们希望为所有群体建立友好关系作出贡献。基督教是和平的运动,因此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加深已注册的中国教会与更广泛的全球教会之间的相互理解。
当WCA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工作时,需要考量哪些敏感的因素?
有许多中国人对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抱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与误解,而世界其他地方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也抱有许多错误观念和误解。
许多中国人认为所有基督徒都像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样——非常反中——或认为我们可能有破坏中国稳定的颠覆意图。但我告诉他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只是想要爱你们。
如果你以错误的观念来接触中国的已注册教会,你会过度戒备,以至于让敏感的情况变得更糟。另外,中国有它自己的规章制度,所以我们要在合法的框架下,寻求接近政府所监管的教会。
我们这次拜访中国,就是为了更多了解他们,了解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我们学习以谦卑的态度来处理双方的关系,就像那些最早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如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样。他们来到中国去,欣赏中国的文化,并与中国人一起服事。
在最近的中国实况调查之旅中,您学到了什么?
WEA的国际理事会在中国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与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金陵协和神学院、爱德基金会(中国的基督教慈善机构)及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商之一(爱德印刷厂)的最高领导会面。WEA国际理事会借此机会见到中国的三自教会,并提出问题。
除了建立友谊外,我们也能进行真实而热烈的对话,提出问题,并邀请彼此成为伙伴。举例来说,我们讨论的其中两个问题是基督教的“中国化”,以及中国试图创造新版本的圣经。我们得以询问与我们会面的不同领袖,听取他们的看法。
首先,他们澄清,他们主要是在探讨“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实践信仰意味着什么”。他们并非在探讨核心教义,例如耶稣道成肉身或耶稣的神性,而是其他方面,例如中国人民如何敬拜上帝或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我们邀请他们与全球福音派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起来做这件事。
在第二个例子中,他们指出他们并非要推出新的圣经译本,而是要修订自1919年首次翻译、广受欢迎的中文和合本圣经。他们说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改动,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和非基督徒更好地理解圣经。我们再次告诉他们,我们有兴趣与他们一起参与修订,以帮助缓和紧张的气氛,澄清沟通上的误解。然后,他们就可以做出中国以外的人也可以使用的译本。
最后,国际理事会的成员非常感谢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领袖,并为这段新关系正向的开始感到鼓舞。
您刚才提到西方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反之亦然,但华语社群内部的误解,例如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间的误解呢?您计画如何将它们连结在ㄧ起?
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总是以联合国为例。全世界的敌人都聚集在那里,因为他们相信联合国的中立性。即使在今天,有些群体正在相互残杀,但他们还是到联合国进行对话。他们如同在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那样,能在联合项目上合作。
WEA并不会在个人喜好或倾向上选边站,而是支持全球福音派的大家庭。我们过往的成绩不言而喻——我们与整个福音派合作。我们希望将所有人包括在内,为所有人提供资源。
散居海外的华人团体对WCA的构想有什么反应?
有些人对此有些顾虑,但我很惊讶地收到压倒性的正面回应。他们说他们一直在寻找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没有预料到会收到如此热烈的反应,这表示我们现在必须以有限的资源非常努力地开展工作。许多团体都问:“你们现在能为我们做什么?你们能在哪些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很感谢大家正面的回馈,但我们目前的工作有点赶不上。
当然,我们过去也曾与一些华人基督教团体有些合作,但从来没有这么全球化。尤其是许多海外事工都很想到中国探访或事奉,但却没有管道。此外,华人基督徒也想向外参与宣教事工,但因为他们只会说中文,他们能去的地方有限。有了WCA,他们可以与非洲的教会合作,用中文与住在那里的华人同胞交流。华人基督徒期待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此外,有些牧师有很好的教材,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传达给全世界,他们只在他们的会众或教会内使用。有了这个平台,他们的教材现在可以走向世界。
这个联盟与世界华福中心现有的交流网络有哪些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在于,华福是从零开始建立的,而WCA则是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散居海外的华人基督徒领袖在第一次洛桑大会的启发下,创办了华福,以连结全球华人教会。另一方面,WCA是代表六亿基督徒的WEA的分支,代表所有基督教教派和团体。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与中国数以千万在已注册教会聚会的基督徒建立关系。正如我们近期拜访中国之旅,WEA愿意与中国政府、注册教会在内等各方合作。这是我们与华福不同之处,也显示出我们是在补充华福的事工,在华福尚不能建立连结的地方建立关系。目前,我们已在几项专案上与华福一同合作。
您对WEA与中国合作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我们希望继续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对话,探讨他们与WEA和地区福音派联盟合作的方式,以及在WCA上的合作。
如果WEA能站在最前线,与注册教会建立善意及合作关系,真的会是很美好的事。我祷告能与注册教会以及其他可能担心、怀疑或害怕与他们建立关系的团体有更多实际上的合作。我们希望能成为一座桥梁,以我们的信仰为锚,屹立在这个地区及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