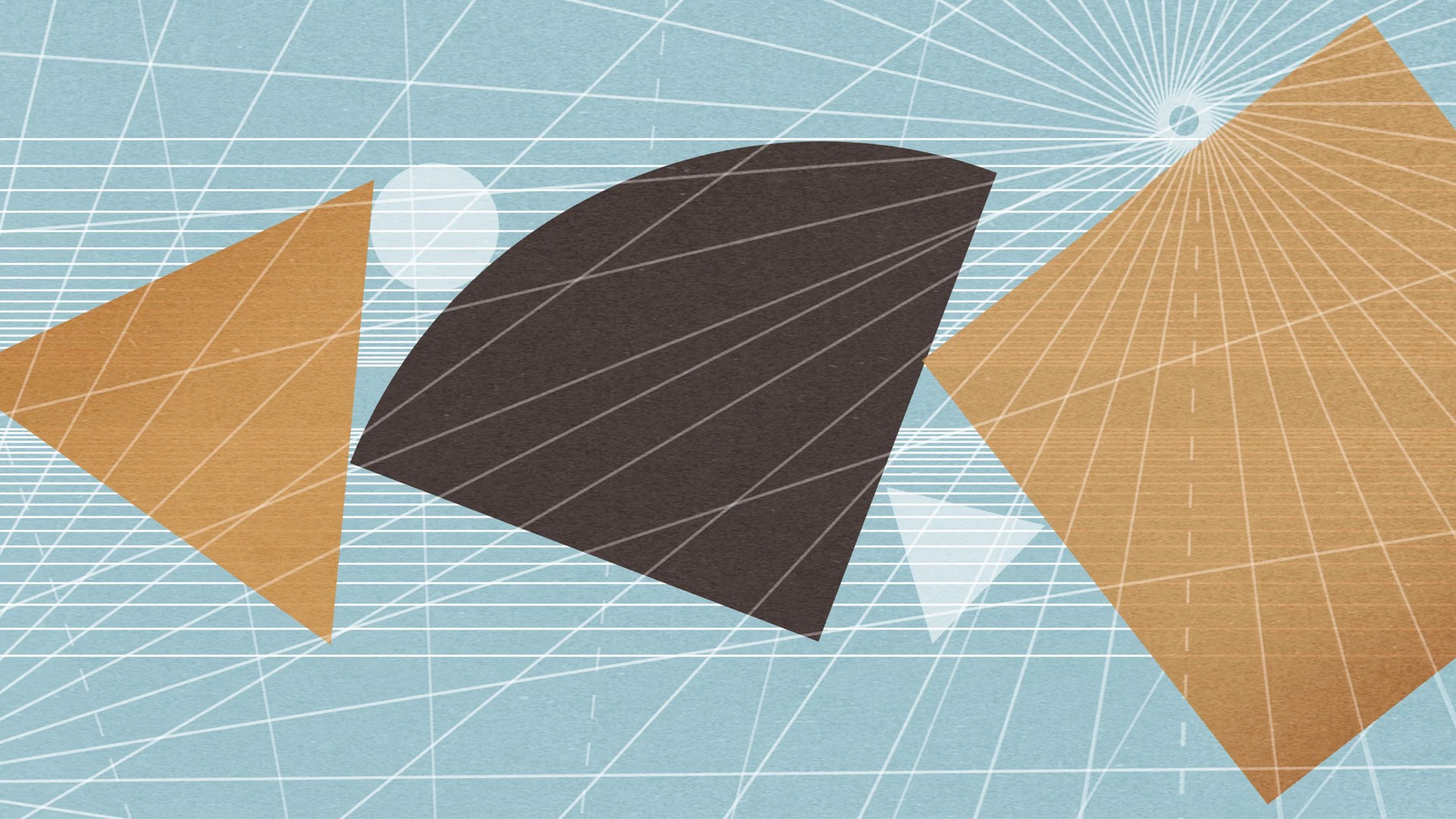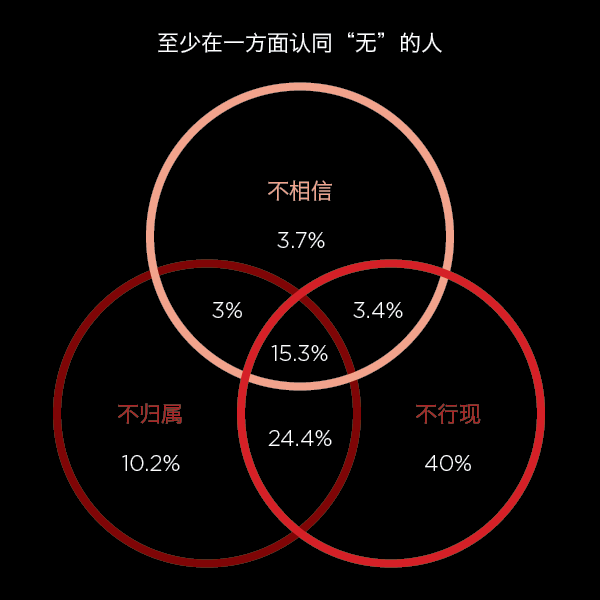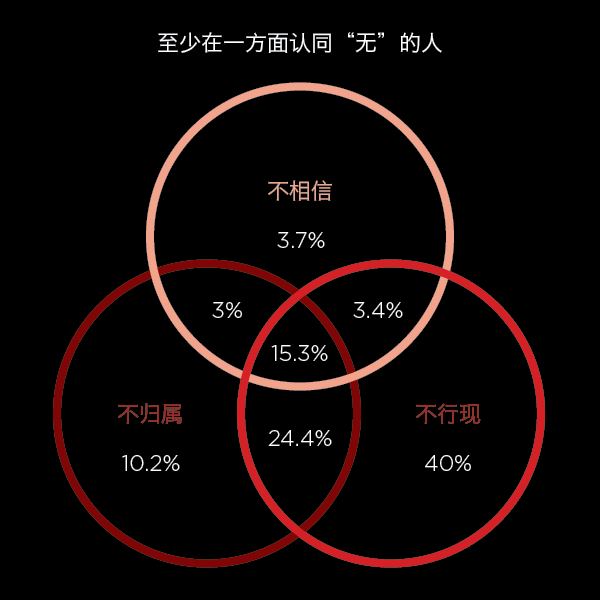总体而言,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圣经和道德持保守态度。然而,根据神学家马太·巴雷特的观察,他们对上帝最基本的宣称往往是显著地具有修正派特点。
巴雷特是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信条杂志》(Credo Magazine)的执行编辑,也是《完全的三位一体:不被操控的父、子和灵》(Simply Trinity: The Unmanipulated Father, Son, and Spirit)的作者。这本书是他2019年旳著作《没有更大的:没有被驯化的上帝属性》(None Greater: The Undomesticated Attributes of God)的续作,它同时做了两件事。首先,它指出福音派神学的三位一体论如何偏离了经典的基督教传统。其次,它募集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最佳老师团队”,他们来自那经典传统,能带领读者回归圣经正统观念的安全港湾。著作的语气平易近人,但内容来源却是深厚的。
福音派是怎样错误理解三位一体的?巴雷特谈及的范围很广,但他着重于被他称为“社会三位一体主义”(social trinitarianism)在近代神学中的发展。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倾向于将上帝的一体性视为一个位格的群体。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立场,而并非单一的学派。巴雷特介绍了一些主要人物,包括自由派神学家,如约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和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及相对应的美国保守派学者,如韦恩·古德恩(Wayne Grudem)和布鲁斯·韦尔(Bruce Ware)。
社会三位一体主义的标志是它愿意将三个位格的关系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典范。对于如莫尔特曼和博夫这样的自由派学者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要利用父、子和灵的平等地位来提升社会平等主义的愿景。诸如古德恩和韦尔等保守派,则有时会利用三位一体内所谓的等级制度——即他们所谓的子对父的"永远服从"——作为他们对性别互补论的基础。 (许多互补论者持不同意见。第十长老会教堂的牧师廉姆·格里格(Liam Goligher)几年前在一篇被疯传的博客中提出了警告,他指责古德恩和韦尔破坏了父、子、灵之间的合一性。)《完全的三位一体》一书做出了透澈的分析,指出三一神学上的修正派趋势是如何进入了看似保守的美国福音派世界。
回归的途径是怎样的?在他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巴雷特重寻三位一体的经典教义,论述了永恒与历史的关系,同时肯定了上帝的一体性和简明性。他所涵盖的教义——圣子的“永恒受生”(eternal generation),圣灵的“永恒发出”(eternal procession)和三一神的“不可分割的工作”(inseparable operations)——听起来相当高深,巴雷特却轻松而清晰地解释了这些教义。
在这些章节中,巴雷特还用了一整章来检视古德恩、韦尔和其他人关于圣子是“永远从臣服于父”的主张。他正确地指出,父、子和圣灵之间的起源关系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对救赎的理解。
这本书并不是完美的。在讨论近代修正派的产生缘由或者经典基督教对三位一体理解的辉煌时,巴雷特都不够深入。而且,对于基督徒灵命塑造这些更重要的问题而言,三位一体的思考该如何运作,他未能做出定位,使这本著作的重点只限制于思想辩论和圣经诠释。
这与经典的基督教思想模式不太吻合。以四世纪教父拿先素斯的贵格利(Gregory Nazianzus)为例,在他的五个神学演说中,他当然论述了有关父、子和灵的圣经经文,但这只是在他为三一论对话作出所需的属灵预备时做出深思后才进行的。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表明,正如《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但是,无论左派或右派的社会三位一体主义,都倾向于犯同一错误,就是把上帝与其他的人做错谬的类比。除非我们解决此根源性问题,否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神学错误的症状不时出现。
尽管如此,《完全的三位一体》努力尝试识别和消除其中一些有害趋势。对于近年阅读过有关三位一体的令人困惑的博客文章的人,这本书将帮助您重回神学正轨。对于那些想重寻崇拜三一上帝的丰富的人,巴雷特肯定是能胜任有余的向导。
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改革宗神学院系统神学的约翰·戴姆·特林布尔(John Dyer Trimble)教授。他是《牛津改革神学手册》的合编者。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