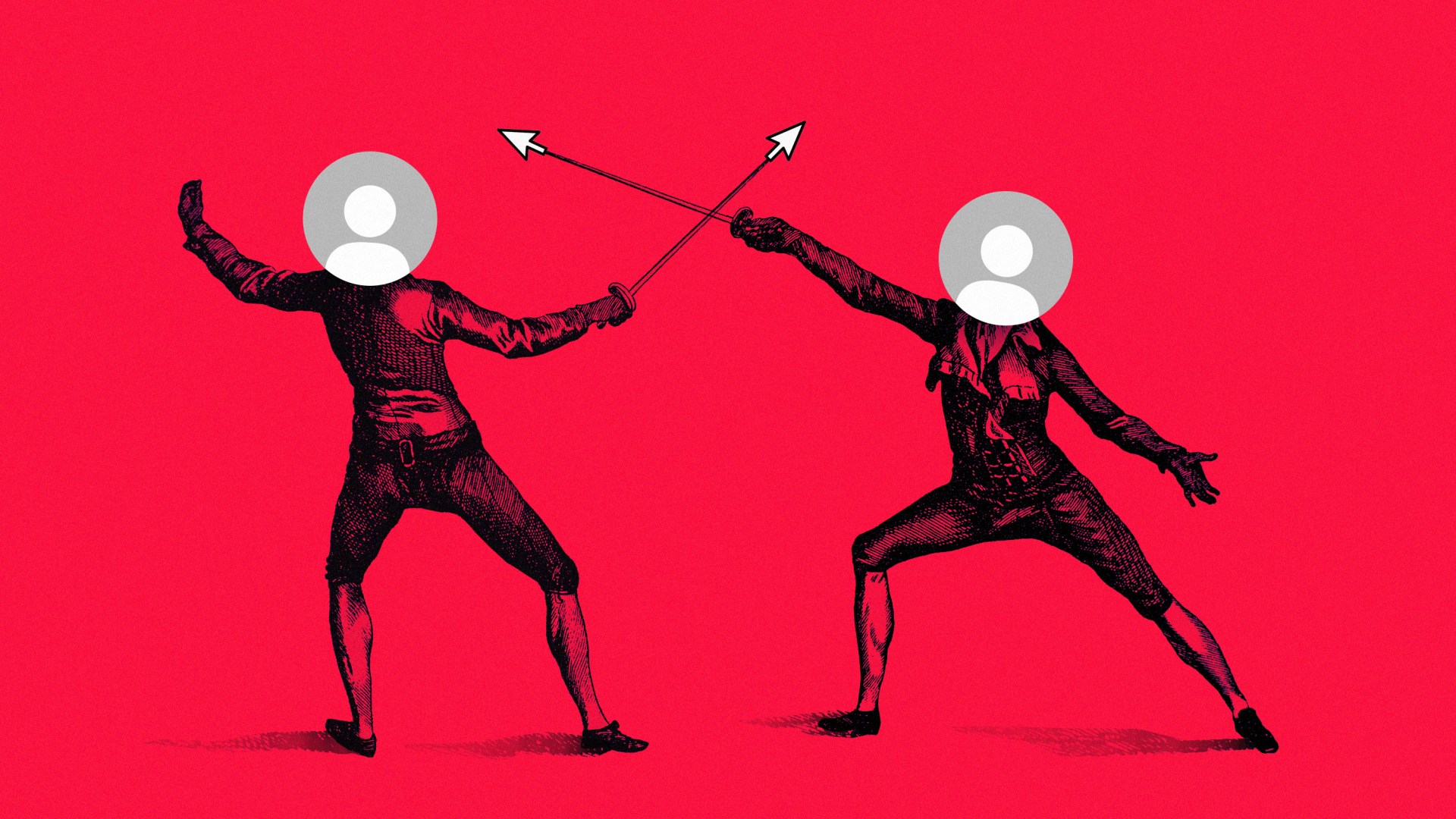现在是选举季,在美国,移民相关问题自然成为公共话题焦点之一,从美墨边境危机到对俄亥俄州的海地移民的评论皆是。而这也是两方基督徒的讨论议题,尤其是最近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福音派基督徒视移民为威胁和经济负担。
作为一名圣经学者,我关注的是基督徒如何解释(或错误地解释)圣经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近期,我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到,有些人声称耶稣鼓励祂的跟随者专注于照顾“自己人”(也就是基督徒),而不是像穷人和移民这样的弱势群体。
其中一种特别的论点引用了耶稣对迦南妇人说的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太15:26),声称耶稣优先照顾“以色列家”(太15:24)而不是外国人。这成为了某些人主张美国联邦资源应优先用于帮助“自己人”而不是移民的依据。
但这种解释真的忠实于耶稣的本意吗?耶稣的话是否真如这些论点充满民族中心思想?简单的答案是,当然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将探讨马太福音的故事背景,并考察另一卷福音书对同个故事更详细的记载(马可福音第7章)。
显而易见地,耶稣是个住在中东的犹太人。祂的民族数世纪以来受制于希腊和罗马的压迫统治。祂的使命是帮助犹太人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认识到上帝的统治。
在加利利长大的耶稣生活在犹太人圈子的边缘地带。因为离耶路撒冷很远,祂的家庭得长途跋涉参加宗教节日。祂生活在犹太、希腊、撒马利亚和罗马文化以及多种语言——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和拉丁文——的交汇处。
在世上传道期间,耶稣主要专注于祂的民族——犹太人。然而,祂对犹太人的优先关注是为了更广泛的目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有意藉由他们祝福全世界。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1-3)。在许多方面,耶稣都在预备祂的跟随者将这个祝福带给非犹太人。
但如果我们将这个计画视为“犹太菁英”向他们的非犹太弱势邻舍提供帮助,我们就搞错方向了。犹太人在这个处境里是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事实上,若要犹太人向非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首先得饶恕那些让他们难以维生的压迫者。
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到以色列边境外的外邦区域,使人一窥祂对犹太信仰圈外人士的态度。马可对这趟旅程的纪录正紧接在耶稣与犹太领袖针对不洁问题的讨论后(可7:1-23)。耶稣才刚说了这句话:“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可7:15)。
当时,食物经常成为区分族群的明显标志。犹太人的食物律法将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包括猪肉、虾和含血的肉)区分开来,这让犹太人视食用“不洁净的食物”的人为“不洁净的人”。当耶稣强调食物不会污秽人时,动摇了“外邦人是不洁的”这一观念,有效地拆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文化隔阂。
然后,为了进一步阐述祂的观点,耶稣带着门徒直赴外邦区域——毫无疑问会遇到食用非犹太食物的人。祂首先到了“推罗境内”,然后经过“西顿”来到“低加波利境内”(可7:24, 31)。虽然耶稣当时并未为门徒点一份猪肉起司汉堡——犹太洁食律依然有效——但祂明显希望门徒开始重新思考他们与食物的关系,因为这会影响他们与外邦人的关系。
推罗是腓尼基的首都,是一个膜拜巴力、梅尔卡特等神明的海岸地区。耶稣在那里时,一位二代移民来到祂面前。这名妇人是希腊裔,但“出生在叙利亚腓尼基”。即便在以色列境外,关于来自加利利的行神迹人士的消息也已传了开来。这位妇人在推罗“就来俯伏在祂脚前⋯⋯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马可形容这个鬼为“污鬼”,将此事件与耶稣先前对污秽的教导联系在一起(可3:7-8;7:25-26)。
然而,接下来的情节令人震惊。耶稣,这位善良的牧者,对她却显得异常严厉:“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7:27)。
作为读者,我们自然会对这样的对话感到不安,因为耶稣似乎侮辱了这位妇人,把她比作狗。在新约时代,犹太人通常用“狗”来形容外邦人,因为他们不遵守犹太律法,被视为“不洁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忽视这段经文的文学脉络。耶稣才刚挑战了犹太人的纯洁观,而这观念正是犹太人民族中心主义的核心,在人与人之间设下牢固的界限,透过区别“神圣空间”来保护“我们”不被“他们”影响。耶稣似乎有意向祂的门徒证明,祂并不害怕走出以色列边界或与外邦人接触。

然而,进入外邦地并不意味着耶稣要展开对外邦人的事工——时机尚未成熟。祂稍后将会吩咐门徒将福音传遍各地,但首先,祂需要帮助祂的民族重新思考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毕竟,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向那些被我们鄙视/认为不洁的人传福音。
耶稣这番看似对妇人冷酷的回应具有双重目的:祂讲出了门徒内心固有的偏见。马太福音15:23记载了门徒的反感态度:“请打发她走吧!”与此同时,耶稣也在向这位妇人提供一个考验她信心的机会。
她是否能认出耶稣的身份,并克服表面上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偏见的侮辱?她是否会同意,自己的祝福需要透过犹太人——这个本身被边缘化的民族?在本质上,耶稣采取了一种街头剧的方式来强调祂的观点。
然而,这位叙利腓尼基妇人立即看穿其中的缝隙,察觉到耶稣暗示她坚持下去的邀请——耶稣可能已预见她会如此反应。毕竟,耶稣使用了“先”这个词,暗示有朝一日,外邦人将直接受益于祂的事工。那么,为何不是现在呢?
“主啊,”她回应道,“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马可福音7:28)。
这位妇人顺利通过耶稣的考验!她巧妙地利用祂的比喻,重申她的请求。她看出了门徒当时无法理解的事——即外邦人也在耶稣的国度中,即使在当时的处境也有一席之地。
马太在他的版本中称这位妇人为“迦南人”以强调耶稣与她的互动展现的正是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间的陈年偏见怨恨,但祂终结了这种仇恨(马太福音15:22)。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并非福音书首次提到迦南女性。在马太福音的耶稣家谱中也有两位迦南人——他玛和喇合——这是早期的暗示,告诉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位迦南妇人(太1:3, 5)。
当然,门徒当时尚未拥有马太或马可写的福音书,因为他们正目睹耶稣的言行在他们面前展开。而我愿意相信马太在推罗与耶稣的经历影响了他在家谱中提及迦南妇人的决定——马太想明确告诉我们,这些妇人应被纳入耶稣的故事中。
我们必须记住,这次前往外邦地的行程是耶稣为了教导门徒的示范课,因他们未能理解耶稣关于洁净的教导(可7:17-18)。耶稣带门徒去户外教学,以展现祂话语更深远的含义,并揭露门徒心中需要改变的错误思想。
在肯尼斯·贝利(Kenneth Bailey)的著作《透过耶稣的中东视角》里,他强而有力地总结这个故事的要点:
耶稣对门徒关于女性和外邦人的态度感到不满。这位妇人对她女儿的爱以及对耶稣的信任让耶稣印象深刻。祂决定利用这个场合帮助她,并挑战门徒内心深处的偏见。在过程中,祂给了这位妇人机会去展示她的勇气及信心的深度。
身为一个加利利难民,耶稣为门徒树立了看待其他“外人”的榜样。透过与这位希腊移民的对话,耶稣给了她犹太拉比绝不会给予的东西:辩论的尊严。拉比们喜欢与人辩论神学细节,但犹太男性从不会与女性进行这种级别的互动,更别说与外邦女子了。
透过充满挑衅的言辞,耶稣邀请她发言,而非让她沉默。表面上看似侮辱的话语,实际上是邀请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最终,他们达成了既尊重耶稣对以色列家的使命,又满足妇人请求的解决方案。在为门徒上了这一堂课后,耶稣医治了这位妇人的女儿,使她脱离恶魔的束缚(可7:29-30)。
简而言之,将耶稣对以色列家使命的言论概括为“照顾自己人”的教导并不成立。这种论述忽视了耶稣教导里的讽刺,也忽略了剩余故事的要义。同样地,若我们利用这个故事来主张美国应开放边界给移民,也是在另一方向上误解了迦南妇人的故事。
无论如何,美国并非上帝的国度。因此,无论我们的政策为何,我们都应谨慎地避免不加批判、未经独立思考地利用圣经故事来支持我们的政治议程。
然而,若我们能从这段看似难解的经文中学到一件事,那就是耶稣的国度是个所有信靠祂的人终将同坐一桌,一同分享食物的地方。每一位在祂里面摆上信心的人都被平等地接纳——“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
Carmen Joy Imes是美国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 )旧约教授,是《Bearing God’s Name》、《Being God’s Image》以及即将出版的《Becoming God’s Family》(IVP出版社)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