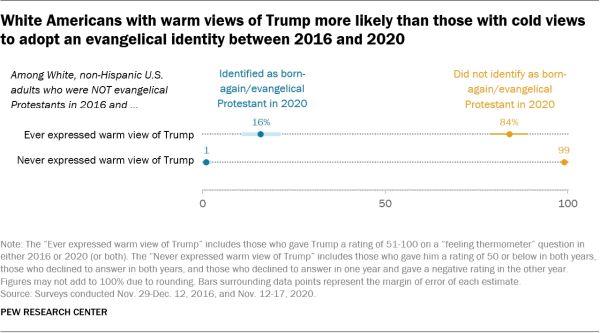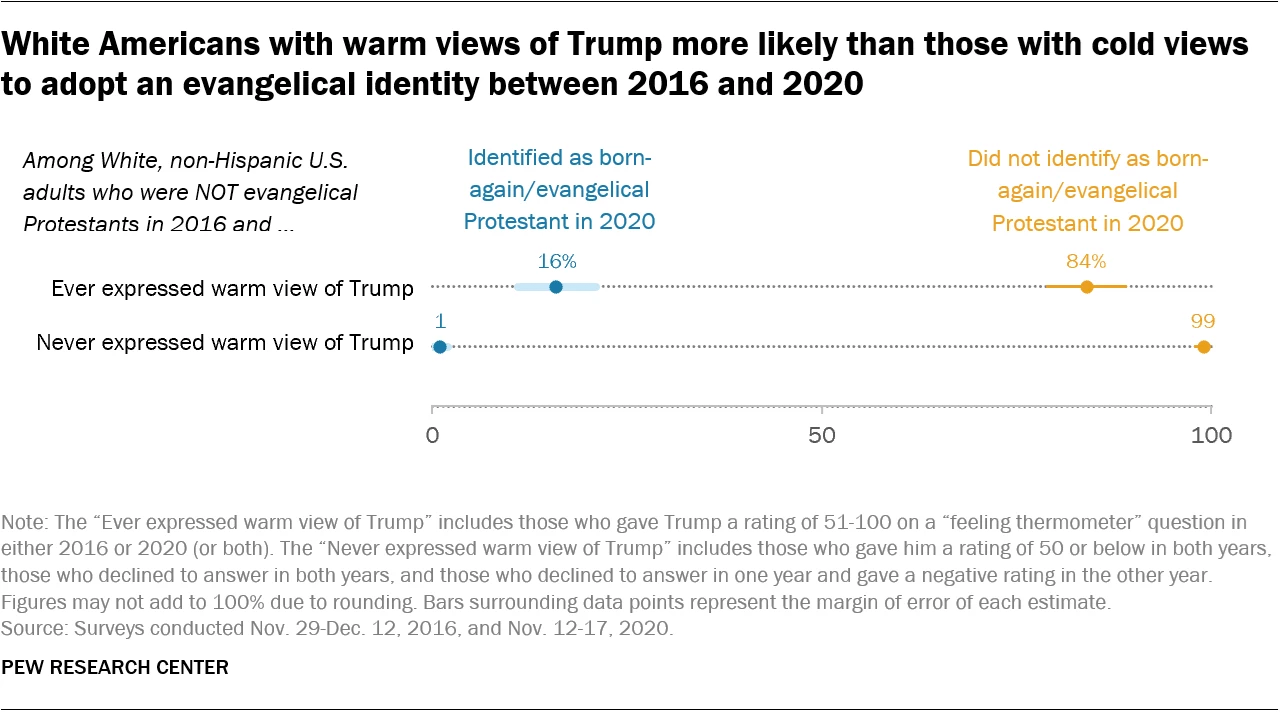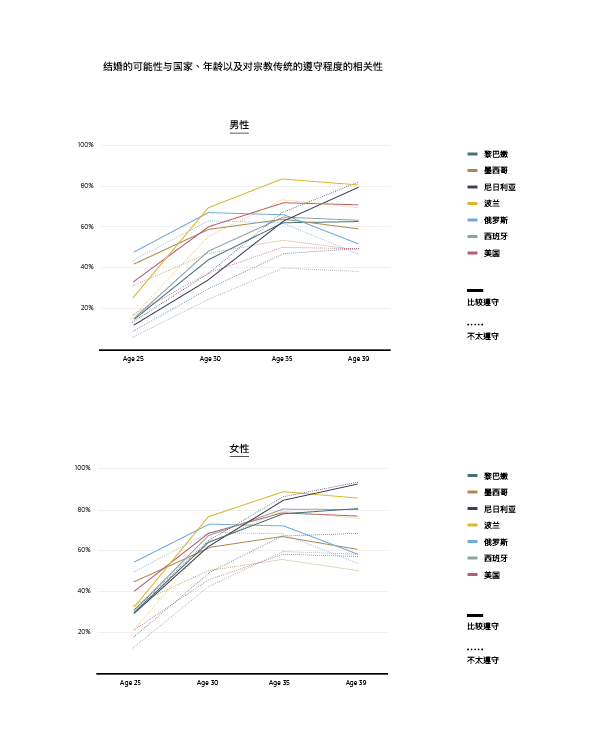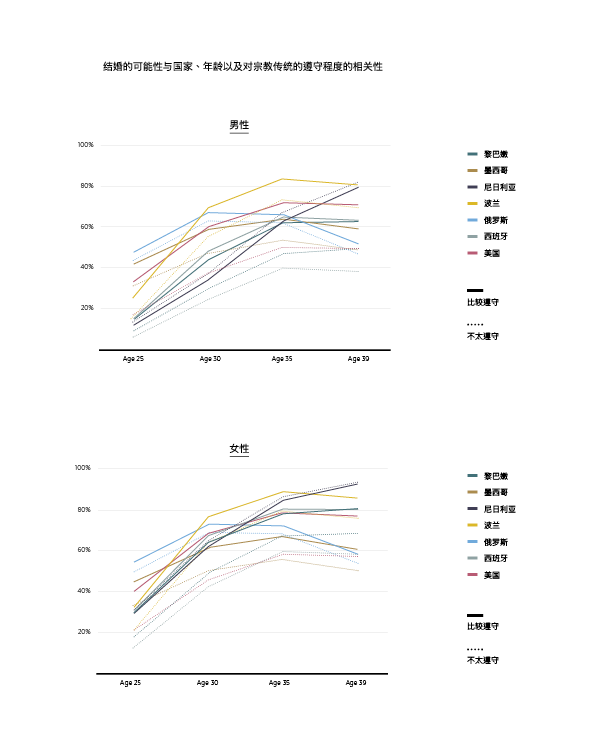上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称哈佛大学校牧团的新主席是一位无神论者。 去年春天,格雷格·爱泼斯坦(Greg Epstein)被其他的校牧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主席。 我是投票给他的人之一。
七年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是受雇于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IVCF)的福音派校园牧师。 我相信《圣经》是有权威的,作为上帝的话语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我相信只有耶稣是救赎之路,若不通过祂,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那么我为什么要投票给一个无神论者来领导哈佛大学的校牧团?
答案在于哈佛大学校牧团独特的、非集权式的运作方式,以及这群来自各个信仰(或无信仰)的领袖们如何在这所常春藤名校里,为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打开大门。 真正的哈佛大学校牧团——而不是在媒体上被扭曲呈现的那个——讲述了一个不同的、非常重要的故事:福音派如何在不损害信仰、真理或使命的前提下,在跨宗教的空间里蓬勃发展。
针对《纽约时报》的报道,许多基督教和保守派 媒体迅速鼓动起宗教人士的委屈感,后者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世俗主义浪潮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明确地表明了担忧,“如果哈佛大学得逞,甚至信仰空间也会被世俗主义者所统治”。
如果自己不是当事人,我可能也会对这个消息有类似的反应。
事发现场当然是一个Zoom会议。 它发生在春季。 我们是一个大约30人的团体,投票选出了明年执行委员会的校牧名单。 我被选为会员委员会主席,格雷格·爱泼斯坦——哈佛大学自2005年以来的人文主义牧师——被选为(校牧团)主席。 大家几乎没有讨论就一致投票通过了决议,并对愿意以各种方式服务的各位校牧表示感谢。这包括前一年我们投票支持的拉比,以及他之前的路德宗校牧,还有她之前的福音派校牧。
一些媒体称爱泼斯坦是“首席校牧”。 还有人声称他 “将监督校园内所有宗教团体的活动”,还有人说他现在正在 “指导大学的40多个宗教领袖”。
这些报告并未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一角色的性质。 哈佛没有“首席校牧”,哈佛校牧团的主席也不指导校园的信仰生活。 我们是一个非集权的、非等级化的独立校牧团体,大约有40名牧师,跨越大约25个教派、组织、信仰传统和宗教。
我们是哈佛的附属机构,但通常不是哈佛的雇员。 在信仰或教义的问题上,我们不向任何上级报告。 我们有共同的承诺,首先是以公平和诚实对待彼此的信仰群体,其次是致力满足哈佛人的精神需求。 我们是一个以共识为基础的群体,往往很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并没有在教义问题上达成一致的预期。
主席从我们中间选出,通常任期两年,为期一年。 这个人主要服务各位校牧——协调、召集和领导我们的会议,以及作为我们和哈佛大学校长办公室之间的渠道。 他们偶尔也会代表我们参加某处的活动。
选择校牧团主席不是为了反映谁的信仰传统占优势,也不是为了奖励最有影响力的校牧。 这些主席并不代表哈佛校牧团有什么大胆的新愿景。 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小组中值得信赖、有能力的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投票给格雷格,因为他很有能力胜任他当选的角色,而不是很多媒体想象的角色。 但我还有更深入的理由:这个跨宗教的校牧团体有益于福音派领袖的事工和使命,包括我和我所代表的组织。
福音派人士历来对跨宗教的项目持谨慎态度。 我在生命中的许多时刻也是如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参与这些项目,前提是不妥协我内心深处排他性的信念。 正如多元信仰邻舍网络(Multi-Faith Neighbors Network)的牧师和创始人鲍勃·罗伯茨(Bob Roberts)所解释的那样。
近年来,福音派基督徒在行动上将自己与社会和文化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 他们这样做有各种原因,但这产生了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教会,而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教会不能忠实地以耶稣的爱来服务和参与世界。 多元信仰使我们不仅有机会为世界服务,也能了解这个世界。
怀旧的情绪让人们起戒心。 我当然为基督教身份 在 任何地方的衰落感到悲哀。 但是,当我们怀念某个被错误记忆的、已经远去的时代,当基督教(几乎)是镇上唯一的商店时,教会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在哈佛的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如果你回溯到仅仅几十年前,福音派基本上被排除在校园的宗教生活之外。 在哈佛大学校牧团产生之前,只有主流新教教会能参与事工。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福音派受益于哈佛对宗教形式多样化的新渴望。
然而,第二个谨慎的原因有一些重要的道理。 福音派人士担心,跨宗教空间往往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所有参与者都要放弃任何排他性主张。这样的担心是对的。 我们怀疑, 跨宗教 往往意味着将所有宗教视为一体,而不是跨越真实乃至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进行交谈和合作。
当我作为学生来到哈佛大学神学院(HDS)时,我怀有这种恐惧。 像我这样持有排他性真理主张的人在某些校园的跨宗教环境中找不到什么空间。 但是,当HDS邀请跨宗教青年核心组织(Interfaith Youth Core)的创始人艾布·帕泰尔(Eboo Patel)发言时,我很惊讶。而他在这个平台上哀叹跨宗教空间没有福音派人士,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演讲中,他没有指责福音派的不宽容,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跨宗教空间。 在为《哈佛神学公报》撰写的一篇相关文章中,他问道。
跨宗教工作的 目的 是什么? 是不是要把不同宗教的神学自由主义者和政治进步人士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不同的信仰如何使他们产生类似的世界观? …… 如果这种方法将信仰团体排除在外,并可能引起对信仰团体的敌意,那么就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认为的在名为“跨宗教”的运动中所做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经验告诉我,跨宗教空间已逐渐意识到排除持有排他性主张人士的局限性。 这种做法最终会将大多数宗教人士排除在外。 作为回应,一种新的方式正在兴起,而哈佛大学的校牧们就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的跨宗教工作采取非集权的方式,鼓励信仰的真实表达——不是来自高校管理者或首席校牧的设想,而是源自教会和宗教组织派来的事工人员及其践行者的 生活。 这种对真正多样性的承诺为福音派教徒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在世界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的宗教领导层中蓬勃发展,成为值得信赖的成员。
本着这种精神,我深深感谢那些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友谊和伙伴关系的福音派校牧,我现在拥有的信任是他们带来的。 我有许多在其他大学从事校园事工的朋友,他们受到多得多的怀疑,甚至是直接的敌视。
我投票给格雷格·爱泼斯坦的部分动机是,我希望在一个跨宗教的空间里建立信任。在这个空间里,人们的观点彼此冲突,而并不假装不是如此。 没有这种信任,福音派就会被贬到边缘地带。 相反,我们在这桌子上,与我们的校牧伙伴一起讨论真理,并承载着希望,在哈佛的多样化宗教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
我把票投给了爱泼斯坦,因为他一直是校园基督徒团契在哈佛最有力的合作伙伴之一。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我们一起参加了前往新奥尔良的服务之旅。他还与我们共同发起了演讲活动。
爱泼斯坦身为校牧,他的使命不是说服人们成为无神论者,而是为那些发现自己没有信仰的学生服务(在哈佛有很多这样的学生)。 他积极寻求我们对有关哈佛校牧事务的看法。 虽然我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意见分歧很大,但他却向这些空间靠拢。在这些空间里,人们可以因自己坚定的信仰保留分歧。 他认为这很重要。
爱泼斯坦在哈佛大学的新角色在基督徒中引发了大量的愤慨。 我能感受到这些担忧,特别是因为《纽约时报》没有为这个故事提供完整的背景。 但是,即使在这个分裂的媒体环境中,我们也应该效法我们的天父,他“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出34:6)。
在博人眼球的标题下,是一个关于福音派如何在跨宗教空间中蓬勃发展而并不妥协的模式。 这是一个福音派人士理应去效仿,而不是去谴责的模式。
Pete Williamson是哈佛大学校园基督徒团契研究生及教师事工的团队负责人,也是哈佛大学的校牧。
《直言不讳》(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嘉宾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本专栏不一定代表本刊的意见。
翻译: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