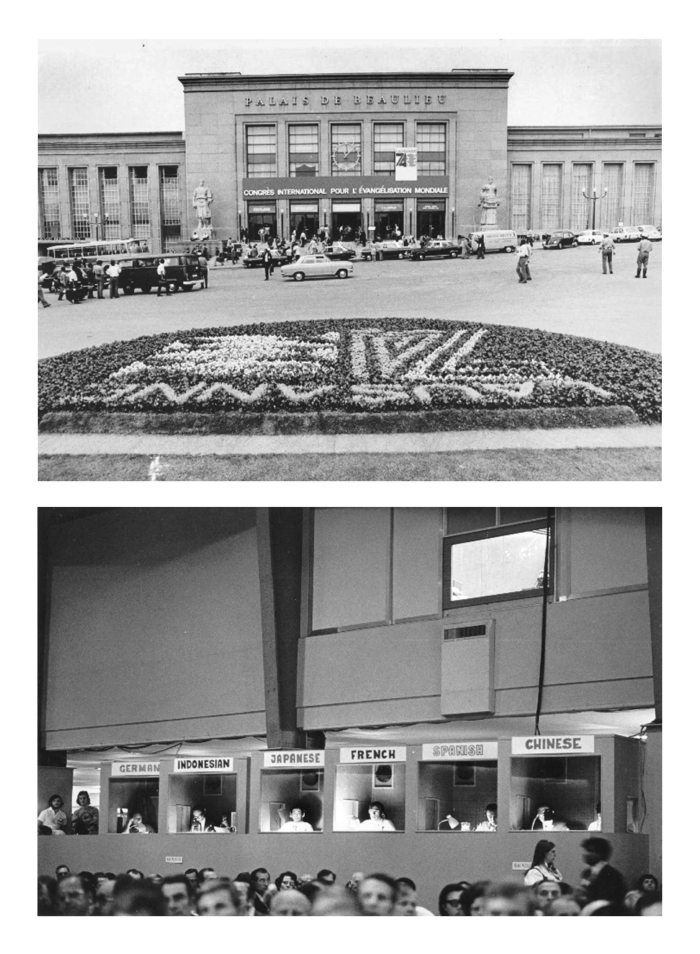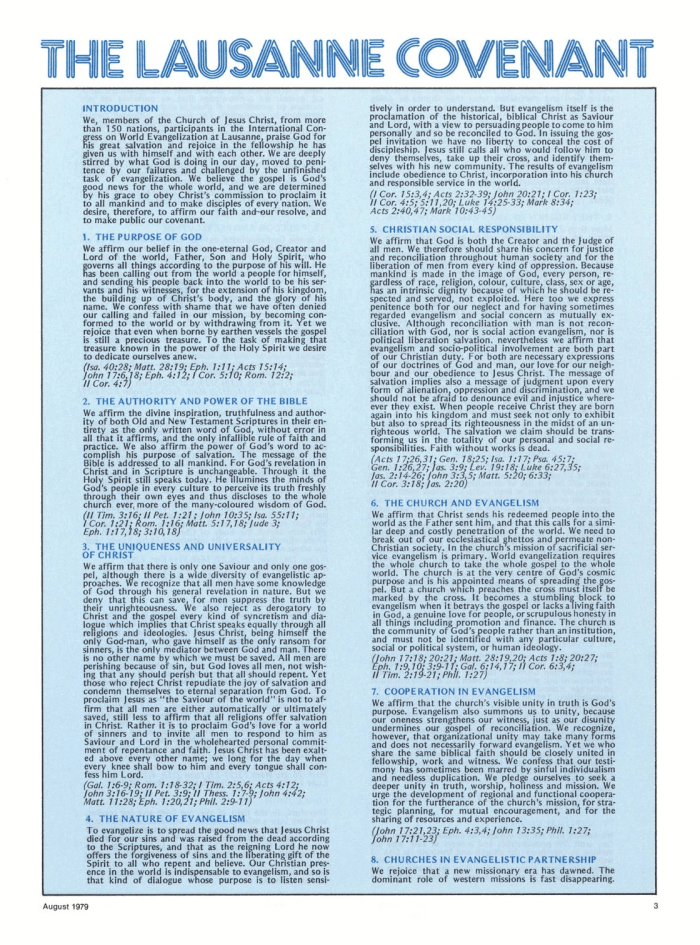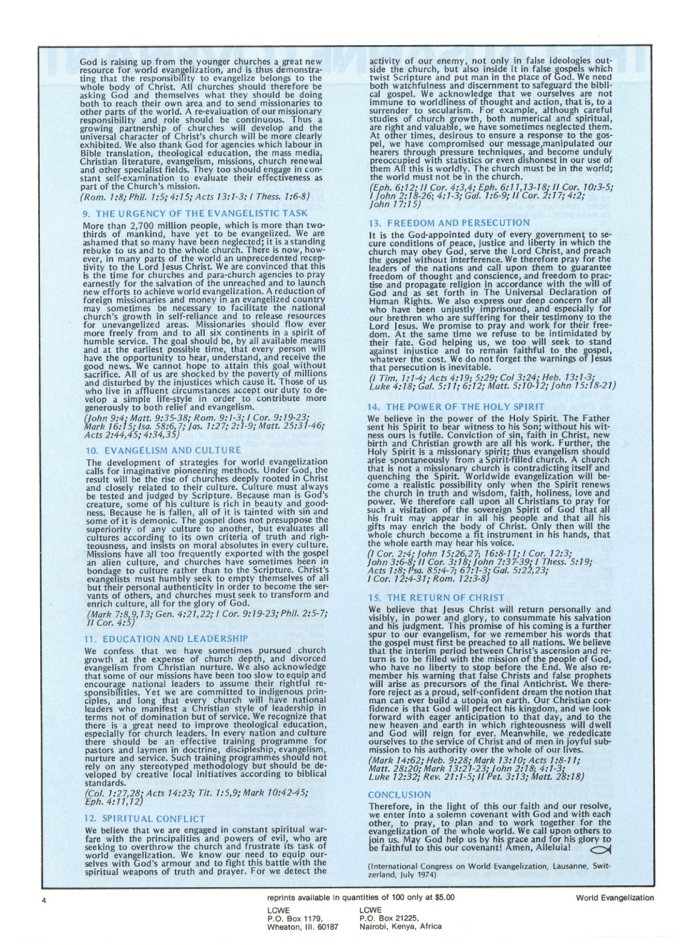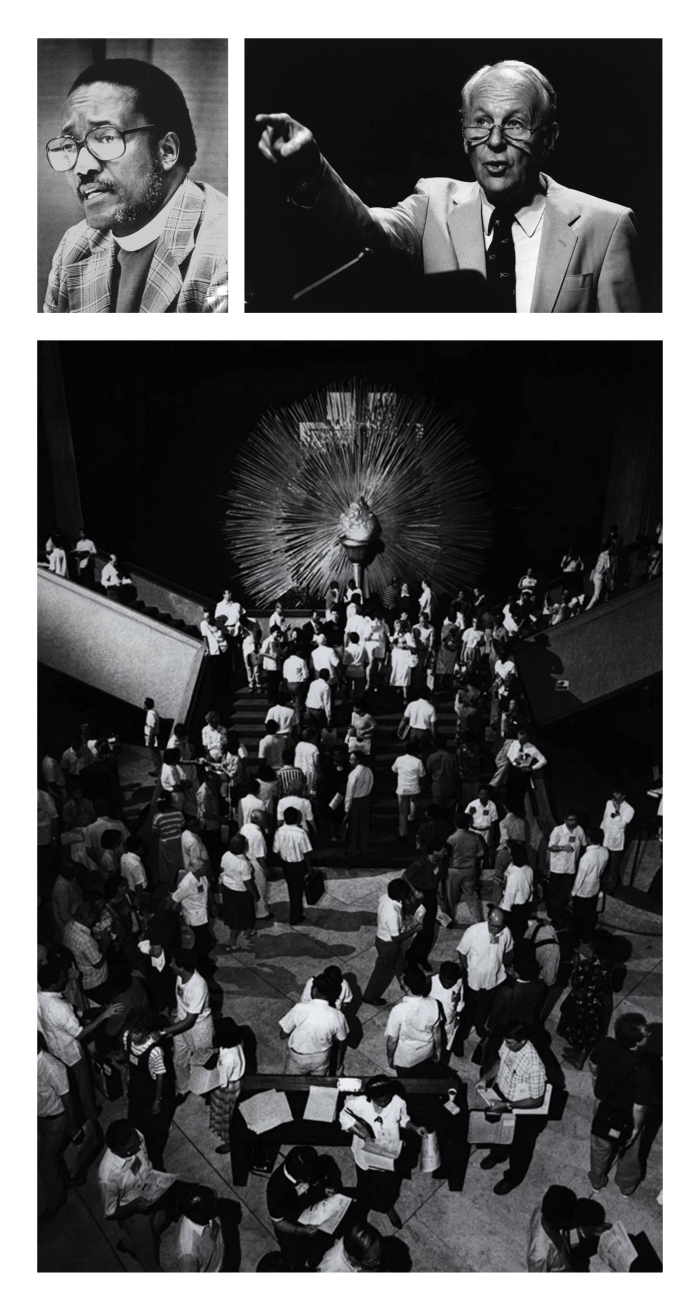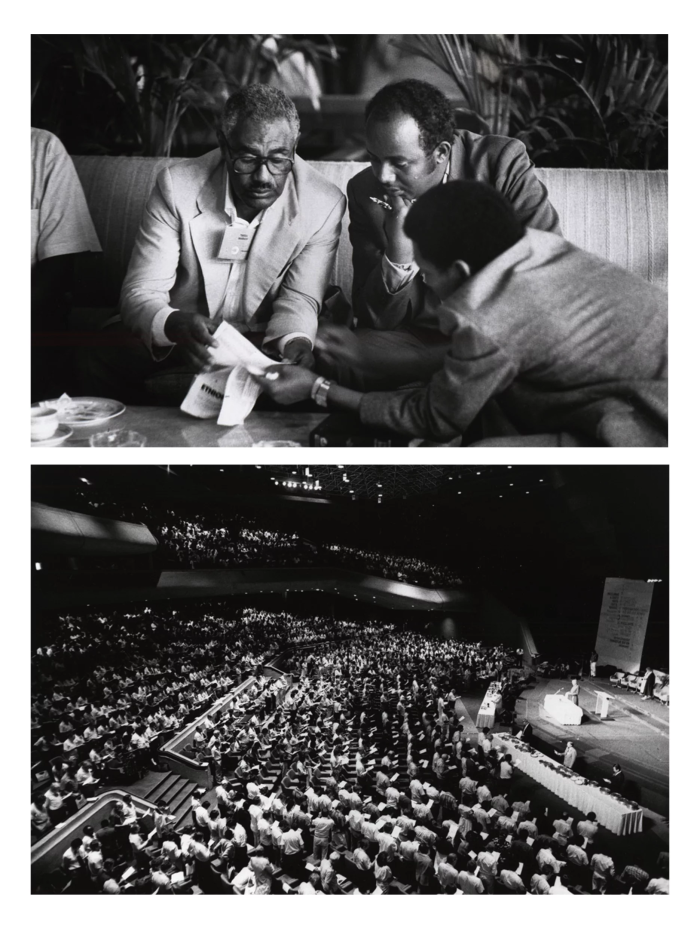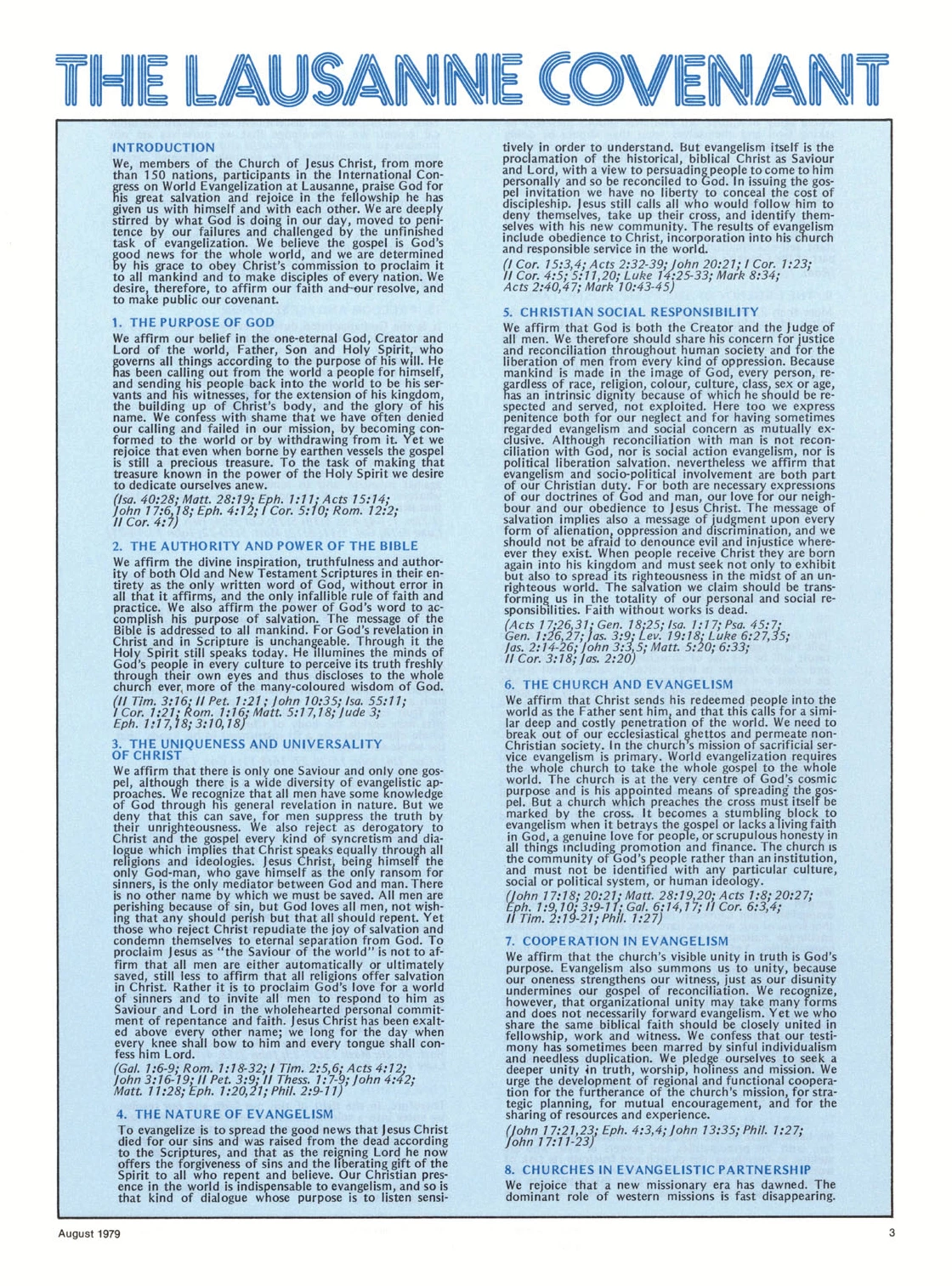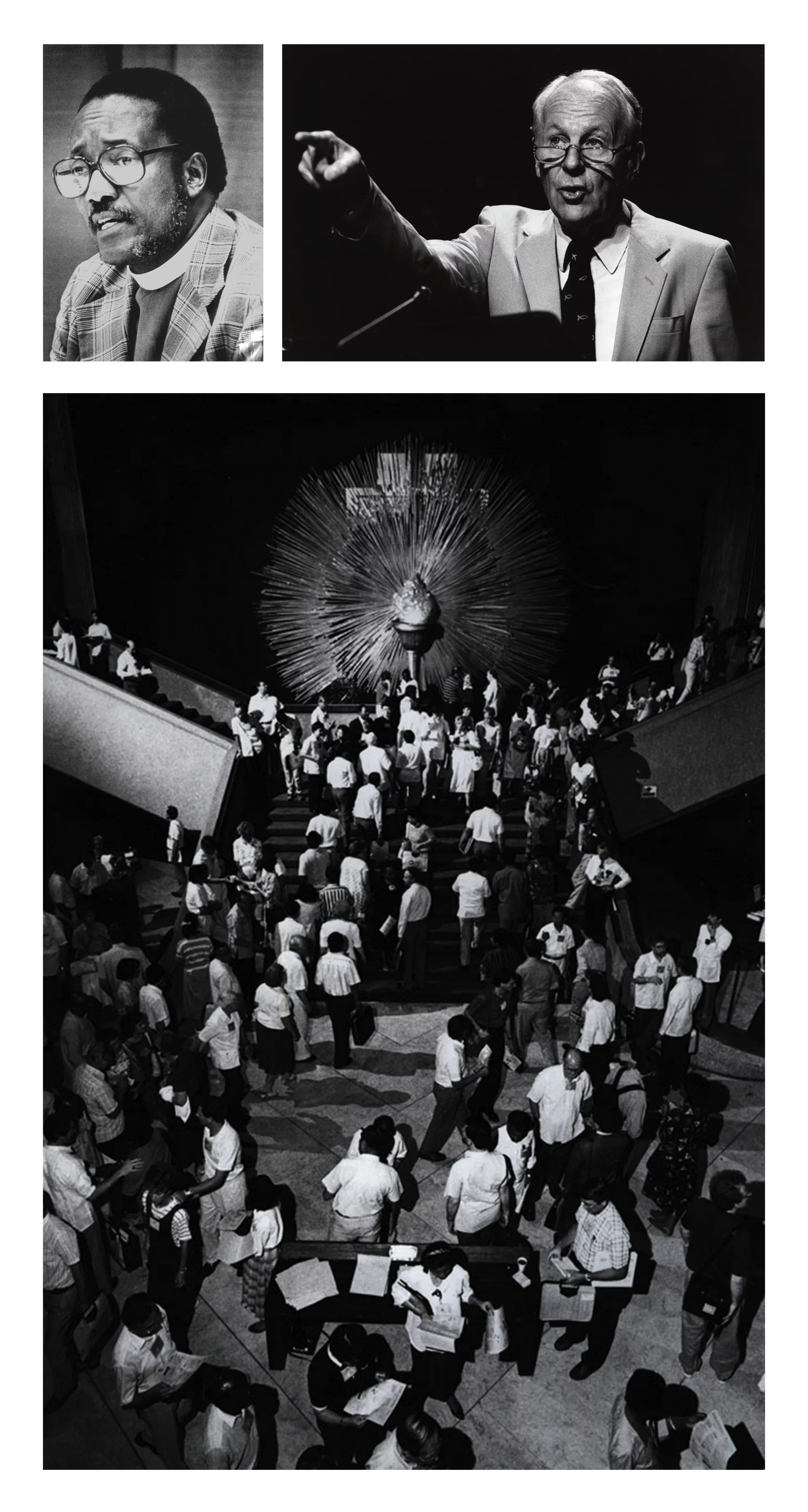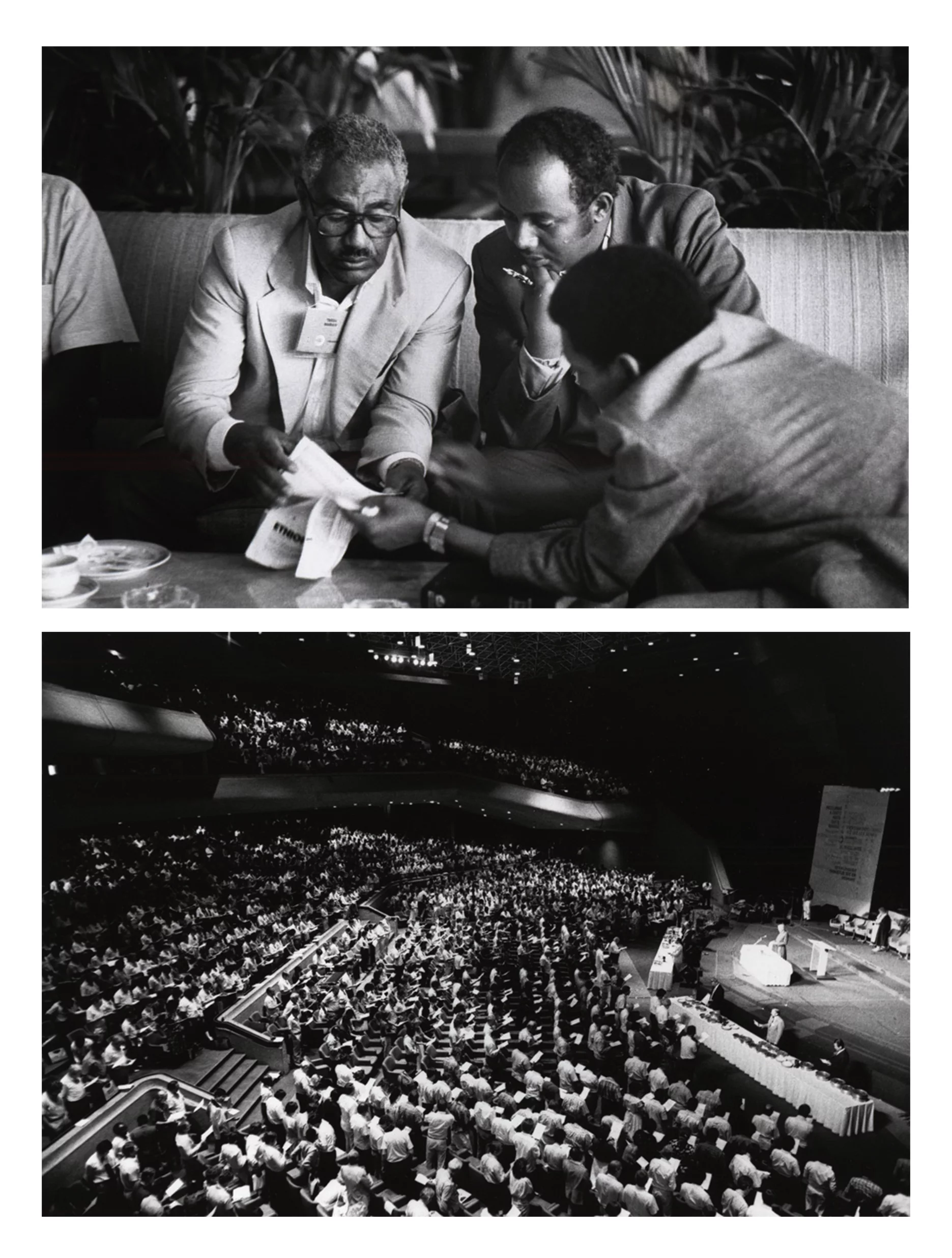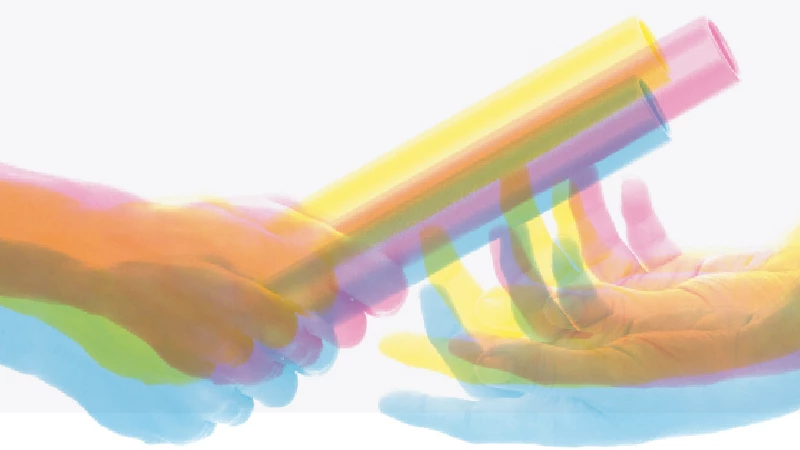我在加州中央山谷(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一间小型福音派教会长大,教会里的蓝领人士比白领人士多。每个星期天大约有25个家庭来到教会;他们充满爱心、慷慨且善解人意。我们曾在内华达山脉露营,背着背包穿越优胜美地,在半月湾设置捕蟹笼。我们会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和遭遇经济困境的朋友分享食物,教会结束后一起去了手指数不清次数的速食店。那是阳光明媚的加州风格的福音派信仰,保守的立场展现在T恤配冲浪裤的穿搭和轻松愉快的态度上。
每当我回想那间教会,尽管它并不完美,我总是满心感激。它使我对随后多年里常听到的“有毒的福音派”刻板印象产生免疫,尤其是在世俗大学里——福音派教会常被描绘成“无知且充满偏见”的堡垒。
当我在2009年选择离开学术界时,ㄧ部分的原因是幻灭。人文科学院对知识探究的兴趣似乎远低于对意识形态一至性的要求。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场博士研讨会上,我的一位同事将整个基督教传教史贬斥为纯粹贪婪的殖民主义。我同意那段历史里有许多值得哀叹之处,但难道我们无法同时承认,肯定有某些宣教士,在那时期的某些时候,确实是带着善良的意图出发的?
从学识研究的正直性来看,这种想法似乎应是和我对话的人至少能接受的。但相反的,她却把我告到教授面前,指控我犯了“为邪恶机构辩护”的思想罪。
这只是我一连串类似的经验中的一个例子。有太多的讲座让人觉得更像是在为政治计画招兵买马,有太多的研讨会让人觉得像是在比赛谁最先表示自己“感到被冒犯”。提出一篇违背人文学科当下的政治正确的论文,即使有再多的证据和论证也不足够;而提出一篇为人所爱的论文,则几乎不需要证据和论证。毕竟,一旦你决心放弃这世上存在单一真理的概念,何不直接选择一个为你和你的部落/群体服务的叙事呢?当你能为人“伸张正义”时,谁还会在乎你的准确性?
于是我离开了学术界,帮助创办一间新媒体企业。如今回想起当年随着部落格圈子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而抱有的理想主义,也觉得实在讽刺。当时,我以为在数位领域里,我们可以重新想像一场富有爱心、知识渊博且敢于挑战党派成见的公共对话。我以为,或许基督徒可以塑造一种公共参与的形式,在捍卫基督教价值观的同时展现基督徒的美德。或许社交媒体可以成为学术圈本应有的样貌:一个思想自由流通的市场,在那里,最好的论点能凭其优点胜出。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新媒体企业建立了能激励人类最恶劣行为的赚钱模式。通往财富与影响力的途径就是病毒式传播,而病毒式传播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煽动部落/群体间的敌意。科技伦理学家Tristan Harris称之为“抵达脑干底部的竞赛”。肯定你受众的既定偏见和预设,激起他们的恐惧,再一起蔑视其他部落——你就能收获大量激情且不断增长的追踪者,然后就能透过演讲和写作获利。
换句话说,建立读者群的最快方法,不是透过长期忠实的工作来建立专业知识和可信度,而是透过迎合某一群体的部落敌意来获得病毒式传播的名声。最初旨在吸引人注意力的行为变成煽动愤怒的农场。
在病毒式传播文化的初期,各阵营的分界线划在保守福音派和进步的主流派等大群体之间。但最后,社交媒体平台显然可以藉由将读者分为更狭小的子类别,进一步提高平台的参与度,并投放更精准的目标广告(也就能赚更多钱)。拥有共同信念的大型社群开始分化,细分为彼此交战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资讯来源,并对周遭的人抱持相同的敌意。我们对所谓背叛我们部落的人所感到的愤怒,远多于我们对那些一开始就不属于我们部落的人的愤怒。
所以,我们来到今天的局面:福音派在嘲讽的市场中被买卖,并彼此对立以谋取利益。作家/内容创作者和观众都沉迷于制造分裂所带来的多巴胺反应。这种情况就像我曾经生活和工作的人文科学院。
一切都被简化为政治立场。只要叙事符合你的部落的利益,事实就不重要了。我们事业的成功不在于爱与理解他人,而在于嘲讽和扭曲地描绘他人。
需要澄清的是,《今日基督教》从未主张基督徒应该退出政治生活。虽然政治不能使死人复活,但却能服事活人。
问题不在于基督徒身处冲突之中,而在于冲突进入了基督徒的内心。我们与彼此、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应该跟随基督的模式,而非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文化模式。
《今日基督教》从未完全符合任何一种群体的政治议程,因为我们对上帝国度的委身远超过对任何党派或国家的利益。我们这样的作法让那些试图定义他人政治/神学派别边界的人感到挫折,但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使命的核心。我们拒绝参与愤怒的循环。
我们的呼召是推动上帝的国度的叙事和理念。无论这些故事是鼓舞人心的,还是艰难的,我们都会讲述。我们邀请正统基督教会的声音来为不同观点辩护。我们努力理解并向社会示范在我们的时代跟随耶稣的真正意义。 《今日基督教》由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董事、行政人员、职员、作家和读者组成。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优势,而不是弱点。
我们在加州中央山谷教会唱过的一首诗歌是《他们会因我们的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曾经深刻经历到基督身体的爱,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记。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3:35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如祂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正是因着教会的合一,“世人知道祢差了我来,也知道祢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彼此表达的爱、向世界展现的合一,见证了基督的神性和上帝的爱的真实性。教会应向世人展现基督的形象,然而今天这形象却充满争议且四分五裂。
上帝的国度总是颠覆世人的期望。在祂的国度里,祂将被世界颠倒的秩序重新恢复到正确的状态。在祂的国度里,祂高举谦卑的人胜过骄傲的人、让温柔的人胜过强大的人、使无权无势的人胜过有权有势的人。祂的国度是最深刻的逆着世界文化而行的文化。
也许此时此刻,基督徒所能做的最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事,就是拒绝将彼此妖魔化。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灵性健全、头脑清晰的基督徒对“何谓彼此相爱的心”会有不同的想法。你的良知要你支持哪位候选人,你就支持他,但让你的爱依然是你起初的爱(启2:4-5),并让我们彼此的爱成为向世界见证基督在我们中间真实活着并工作的标志。
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兼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