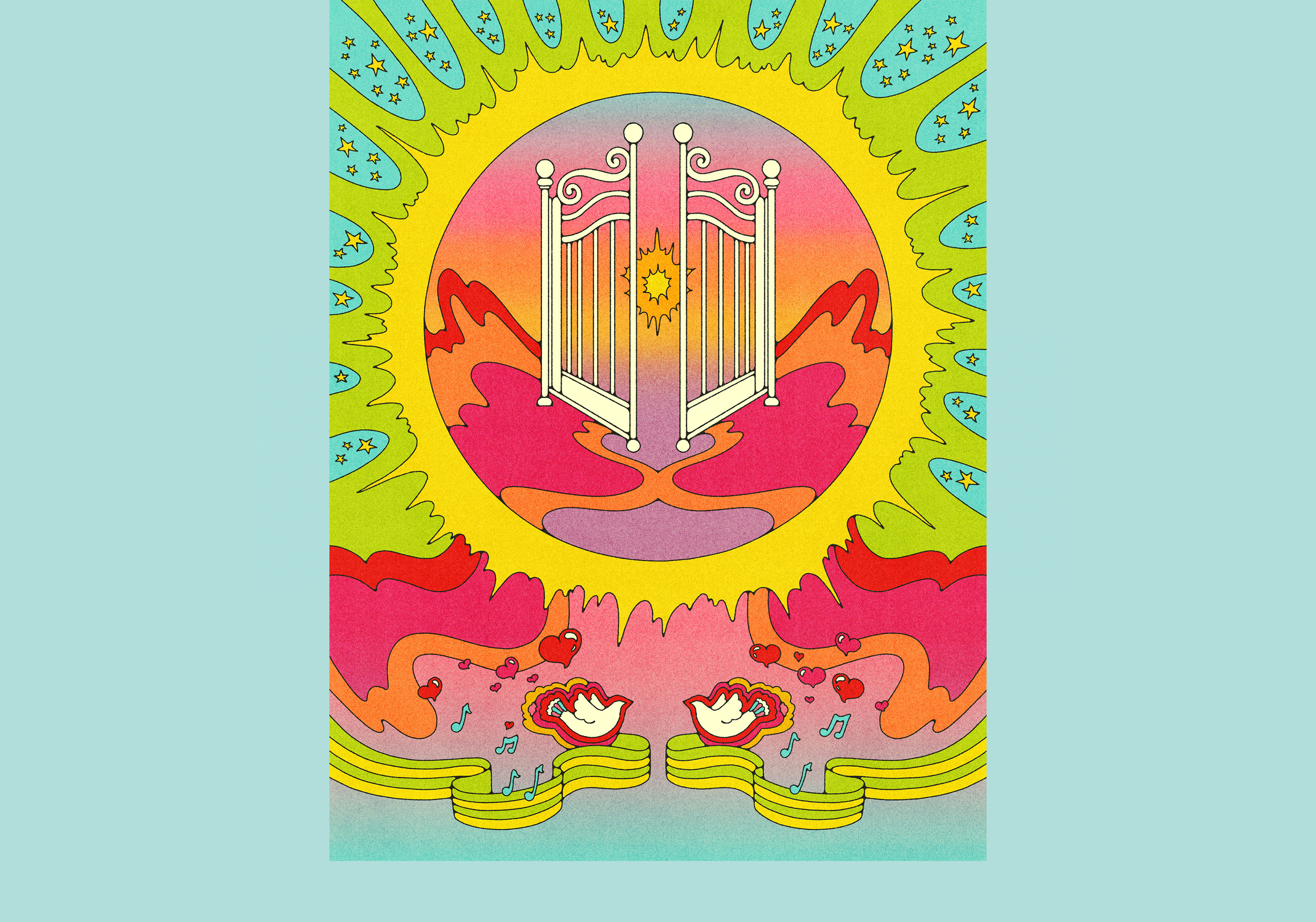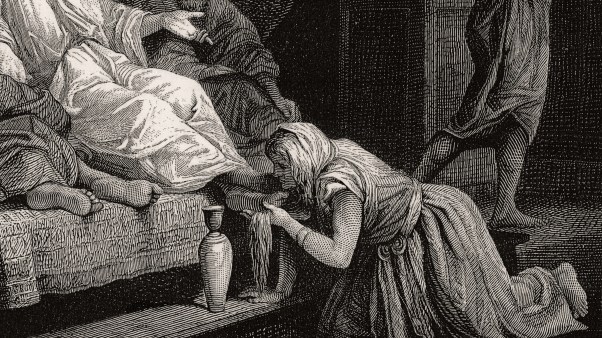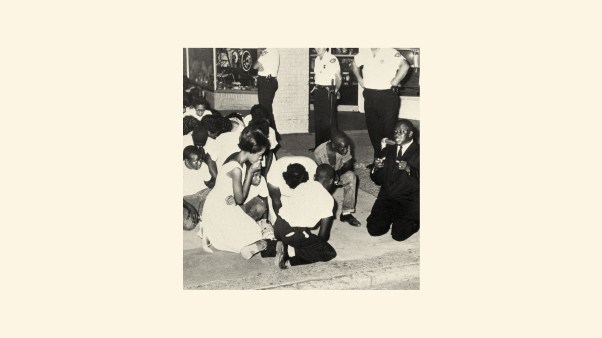当我还是个不可知论者时,我以自己拥有 “开放的心态” 为傲。
我倾听各种灵性理论,从佛教经典到加尔文主义宣言皆涉猎。我的研究真道之旅领我参与了俄罗斯正教的宴席,以及摩门教的历史庆典。我在这些我不信其所指之神的诸般途径中,都能找到值得欣赏之处。但有件事,当时的我却如信奉教条般坚持:如果上帝存在,祂绝对不会认可当代基督教音乐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简称CCM)。
我其实说不清这种偏见从何而来。我平时对音乐并没有强烈的意见。直到近期,我什至也叫不出任何一首当代敬拜歌曲的歌名。原则上,我通常会为福音派辩护,反击别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记者,多年来我听过太多福音派基督徒自己对当代基督教音乐冷嘲热讽,以至于对这种音乐的轻视似乎成了一种人们可接受的偏见——甚至成了和 “内行人” 建立连结的方法。
2008年某个周末,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参加位于芝加哥西北方、以 “慕道友友善” 著称的巨型教会,柳溪社区教会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举办的研讨会。早上刚结束关于巨型教会门徒训练未来方向的讨论,灯光便暗了下来,舞台上方的萤幕开始闪现歌词,贝斯手拨出第一段和弦。我记得自己坐在会堂后排,在震耳欲聋的黑暗中眯着眼看笔记,心想:在教会里办摇滚音乐会,肯定是不对的。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我其实觉得旋律有点好听,但这反而更加深了我的不以为然。
和多数不信主的人一样,当时的我对 “神圣” 与 “世俗” 之间的界线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想法。然而,我却极其笃定:用好几把吉他、电子琴和鼓组唱关于耶稣的歌,是十分亵渎的事——更不用说最后会众那粗俗的掌声了。在我那时缓慢蹒跚的灵性探索旅程中,我从未读过《诗篇》,因此完全不知道《诗篇》确实如此要求敬拜者:“万民哪,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诗篇47:1)
然而,距离我在芝加哥郊区第一次听见那 “神圣的杂音” 后约14年,上帝终于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令我意外的是,祂选择在一间巨型教会里成就此事;而且并非 “尽管” 背景里有着当代敬拜音乐,而是 “正是” 那些简单的歌词与洗脑的旋律大大地助攻了一把。我为自己过去的高傲态度悔改,并且如今能在更宽广的视角下看待这些音乐和我自己的反应。
今日围绕着当代敬拜音乐的争吵,其实是历代以来屡见不鲜的辩论的最新一章——我们究竟如何在保持福音完整性的同时,触及到所处的文化?我们又该如何设计一场既能牧养基督徒、又能吸引未信者的敬拜?我在摸索的过程中学到一件事:我们对某件事物的 “本能排斥”,也许正是上帝要用来使我们谦卑的路径。
但基督信仰所传递的信息,对这个世界而言本就是陌生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
基督的道德要求,在不同年代都以不同方式刺痛各种社会;但就本质而言,基督徒坚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典,并且永远无法靠自己赚得恩典;这个信息对人类骄傲的心而言,永远是极其冒犯的。更甚者,基督徒还宣称:在这个充满邪恶与苦难的世界里,上帝的爱仍能合理地存在,并且两千年前,这一切苦难在一位被钉在罗马酷刑器具上的人的死亡里,永远地解决了。
保罗称这一切信息为 “绊脚石”。他花了整个宣教人生努力使这个信息更容易被人理解及接受。这意味着他得不断进行 “文化翻译” 的尝试——他称此为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前提是不能因此粉饰基督信仰中最 “怪异” 的主张 (林前9:22)。广义来说,今日的当代敬拜音乐,是两千年来无数传道人与艺术家努力效法保罗,以音乐吸引慕道者、门训基督徒、和敬拜上帝的传承。
美国第二次灵命大觉醒时期的圣诗作者曾借用小提琴舞曲、吉格舞曲、里尔舞曲,以及其他世俗领域的旋律。历代以来,试图把世俗音乐改编为教会使用的基督徒,并非每次都能成功,而且总是会惹恼、冒犯其他基督徒。五十年前,诺曼 (Larry Norman) 与其他耶稣子民运动 (Jesus People) 的人,将摇滚、福音、民谣与传统圣诗混合,再配上涉及 “情人节淋病” 之类不太雅观题材的歌词。基督教书店店主对是否上架他的专辑犹疑不决,甚至把唱片藏在库房或柜台底下,“怕有人走进来指责他们卖这种东西”。
虽然一些基督徒至今仍担心摇滚乐被性与毒品玷污,但到了1990年代,最受欢迎的敬拜乐团与基督教流行歌手,已不再主要迎合叛逆青少年的口味,而是主攻那些想让孩子远离MTV的富裕郊区妈妈们。
也因此,今日的评论家们更常哀叹敬拜音乐的 “乏味”,而非 “低俗”。在一则名为 “为什么现代主流基督教音乐这么无聊?” 的讨论串中,一位留言者写道:“所有歌听起来都一样,不断重复一样的和弦及声线”。一位名叫约书亚 (Joshua Sharp) 的牧师则在Baptist Standard专版上抱怨:“多数现代敬拜歌的歌词,只是成功神学加上廉价的心灵鸡汤”。
美国巨型教会敬拜事工的 “四巨头”:伯特利音乐、Elevation、Hillsong、以及Passion Music——以环境系流行摇滚的声响,主导了整个当代敬拜音乐产业。我ㄧ位不可知论者朋友对这现象的总结是:“就只是对U2乐团的拙劣模仿”。与雷鬼或福音音乐不同,这类型的主流诗歌没有任何鲜明的音乐特征。西敏寺神学院教授兼牧师克拉克 ( R. Scott Clark) 甚至写道,这类音乐 “在美学上和真理教导上都很空洞⋯⋯多数当代敬拜音乐的主要功能,就是产生一种轻微的陶醉感。”
不过,正是这 “轻微的陶醉感” 帮助了我归信基督。
诚然,这些歌的歌词很简单。但除非你盯着投影幕上的字体时,从未认真思考那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否则,说它们都很 “空洞” 并不公平。如果深思过后,发现你教会敬拜时的歌词真的很空洞且毫无实际的神学意义,请尽速逃往离你家最近的一场会合唱古典圣诗的礼拜吧。
真正定义当代敬拜音乐风格的,其实是一种 “不协和感”:平滑的和声、简单的歌词,以及当你稍作停顿去思考歌词意义时,所感受到的冲击反差。
想ㄧ想伯特利音乐2019年的热门歌曲,〈神的良善荣美〉(Goodness of God) 开头的几句歌词:
I love you, Lord (主,我深爱祢)
Oh your mercy never fails me (祢的怜悯永不改变)
All my days, I’ve been held in your hands. (每一天,祢的恩手扶持我)
这19个字每一句都大胆到令人咋舌:一位全能的上帝认识并关心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细节;祂不只爱我们,甚至为渺小的人类开启一条能够回应祂的爱的道路。
的确,这是幼儿园程度的基督教神学;但耶稣告诉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祂面前。如果我们紧抓着这个世界 “成年人的” 公平观及权力观,或以成年人的 “常识” 来定义上帝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祂。
敬拜中那份 “轻微的陶醉感”——社会学家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 形容为 “集体亢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的状态——有时确实可能只是类似异教徒的摇滚演唱会快感。然而,对许多人而言,这种感官经验与易唱旋律,就像父母的手轻轻按在幼儿背上,引导我们走向圣经所说的 “敬畏耶和华” 之心。这通常不是什么神学上的突破,也不是神秘经验,更像是羞怯而侧面的瞥见救主荣面——瞥见那位面容 “如同烈日放光” 的救主 (启1:16)。而对多数人来说,如此一瞥,已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最大程度。
一段容易记住的旋律,加上一条在胸腔震动的低音频,往往能瓦解我们的防备。它们能打开心灵的眼睛,使人看见基督教基本信条中那幅极度违反直觉的永恒图景。这些音乐会卡在我们脑中,整天持续在我们里面运作。最近刚在麦克莱恩圣经教会信主的布莱恩 (Bryan O’Keefe) 告诉我:“当我聆听这些歌的时候,我开始把歌词跟自己的人生经验连在一起,然后它们开始让我感觉自己被带进一个更庞大的事物里。”
敬拜音乐理当同时是 “安慰的食物”,也是 “苦涩的良药”。至于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安慰人心、或震撼人的味蕾,则取决于个人品味与文化处境。这或许正是为什么上帝安排——或至少允许——现代教会呈现如此惊人的多样性 (学者估计,全世界基督徒分属近五万个宗派、信仰传统或教会联会)。毕竟,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 “刺棒” 来推动。
我认识一些在偏浸信会、无宗派背景教会长大的基督徒,后来走向圣公会、天主教或东正教传统——因为古老礼仪的文字与节奏,能将他们从21世纪的美国泡泡中抽离,帮助他们重新找回那能传遍全球的福音的奥秘。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却需要走在反方向的灵性之旅上。
是中世纪的合唱编曲与萦绕的香烟,引领我踏入最初的信仰探索。我长大的过程没有任何宗教背景及经验。大学期间,我因着对俄罗斯文化、语言及神秘主义的兴趣而开始研究东正教。在研究所期间,教会历史课又把我带进学校附近的英国天主教教会。
我爱上了这些传统——至今仍深爱它们——正因它们那种毫不掩饰的 “奇异感”。我渴望一个与现代美国科技加持下的极致个人主义彻底不同、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他乡的空间。那些致力保存古老形式、对过去一世纪的流行歌浑然无感的东正教及英国天主教教会,正提供了像这样的空间。
问题在于,对我这种不可知论者、热爱教会史的书呆子而言,一个充满雕刻物、苦像与彩绘玻璃,以及繁复礼仪的空间,给了我无限分心的契机,神游四海地想着许多与耶稣无关的事。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向牧师赞叹,去教会让我感觉与西方文明连结更深了 (他人非常好地没有责备我)。当然,我如今也并非想跟16世纪的 “破像派人士” ㄧ样抨击这类教会礼仪传统 (虽然我完全能理解慈运理的立场)——我想指出的,只是我个人那点不甚高明的骄气、个性,以及人类喜欢逃避艰难事物的倾向。
我曾连续聆听俄罗斯修道院圣歌的CD好几个小时,一心想着破解古教会斯拉夫语(我修过一学期),以至于我从未真正面对那些修士所赞美、所恳求怜悯的那位上帝。主日崇拜时,我坐在后排,心里想着我有多喜欢在〈公祷书〉的悔罪文里承认及哀叹自己多重的罪与恶;甚至在成为有神论者之前,我就觉得 “原罪” 这个教义很有道理。然而,我的心思更常飘向的是这些优美词句的文学光彩,而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或明白是因着祂的受死,全然败坏的人类得以有胆乞求赦免,甚至大胆地相信自己真能蒙赦免。
后来,我渐渐不再去那间英国天主教教会。对我而言,相信上帝仍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命题,更不用说理解何谓道成肉身了。我很感激那些没有追问、也不强拉我去团契茶点时间的基督徒。但也许,是时候承认我是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 形容自己时所说的,是个 “在宗教上没有音感的人” 的人;韦伯一生研究各种世界宗教,却从未宣称相信任何一种。
博士毕业后,我又花了十多年读书、查阅档案、访问基督徒、授课,做着所有让我成为 “美国基督教专家” 的事情。我并不喜欢身为一名不可知论者,但我接受了自己的状况,毕竟我已找遍所有 “宗教医生”——至少是那些有声望的医生——却没有一个能治好我。
我的故事虽然独特,但我想说的道理却非常普遍:人很容易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已经 “弄懂” 基督信仰,实际上却只是把基督教的上帝改造成符合自己喜好的神明。
直到大约三年前,上帝伏击了我。
当时我正在为一本杂志撰写一间位于罗利的美南浸信会巨型教会,顶峰教会 (The Summit Church) 的专题报导。他们的牧师葛瑞尔 (J. D. Greear) 把我们第一次的访谈变成了一场不断延伸的对话。他逼着我意识到,我需要真正检视基督教对人类历史所提出的主张 (而且已有许多书籍精细地处理了这些问题)。我本该多年前就读这些书,甚至需要读它们的每一则注脚;若不是这些研究,我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承认新约文献是可信的史料、并且 “耶稣复活了” 是对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的最可能的解释。
然而,在我艰辛地啃着赖特 ( N. T. Wright) 的《神儿子的复活》等书时,我也持续参加顶峰教会的主日礼拜。每个周末,我坐在礼堂后方最上层、柔软有靠垫的座位上,盯着巨型萤幕上的歌词。我什至会开口唱,因为周围又黑又吵,没人能看见或听到我的歌声。没错,那感觉就像在演唱会上——但对我而言,这个演唱会除掉了那些我曾在教会里把它们变成偶像及借口的东西。
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唱着 “我们透过血、借着父神得救赎” 一点也不俗气。而Charity Gayle的〈Thank You Jesus for the Blood〉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盘据着我的脑袋,也并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
是的,人们对当代敬拜音乐的某些刻板印象,确实说中了要害。有不少歌曲把上帝的得胜与祂对子民的看顾当作主要主题,较少着墨于罪与受苦。例如Tauren Wells在2020年的作品写道:“在水中为我开路/带领我穿越火焰/成就祢所闻名之事”;或如Passion Music这首歌的歌词:“没有任何事是我们的神不能做的/没有祂不能挪开的高山。”
敬拜事工四巨头里,有三个偏向灵恩传统,而虽然Passion City教会属于较广义的改革宗,但灵恩及改革宗传统两者皆强调基督复活所带来的 “那改变生命的大能”;当然,这确实也是新约的重要主题之ㄧ,尤其在保罗书信中。
如果公共敬拜的目的,是当日常生活把我们往反方向拉扯时,将我们重新牵引回敬拜造物主的姿态里,那么,唱ㄧ些能提醒我们基督在永恒里胜利的诗歌——终有一天,祂将除去世上一切痛苦——就完全说得通,即便我们现在仍身处苦难之中;正如Vertical Worship的〈Yes I Will〉副歌所唱:“是的,我要在最低的山谷高举祢。”
而有些当代敬拜音乐旨在培养 “特定的属灵经验”:某种与上帝亲密连结的感受——也就是批评者嘲笑为 “耶稣是我男友” 类型的歌。这类歌曲若没有全面的圣经教导作为基础,的确可能助长一种肤浅的情绪状态,比起顺服基督,更像初中生的荷尔蒙波动。但即便在这种状态中,同样也可能有更深层的事正在发生。音乐人Melanie Penn曾告诉我,她认为自己像某种 “心脏医生”,打通人们头脑与心之间的动脉。
例如Maverick City在〈Communion〉里唱道:“祢比我的皮肤更贴近我/祢在我呼吸的空气里……这就是我应在之处 (就在这里) /我在祢里面,祢在我里面”。歌词里的意象与圣经作者们相当一致:他们常用婚姻与爱情的比喻,帮助有限的人理解上帝盟约之爱的深度。在中世纪,《雅歌》甚至是修士们最喜欢书写的经文之一,但不是因为他们是太过压抑的独身者,而是因为他们真正理解因基督的牺牲所成就的神圣亲密感,是何等惊人。
说到底,没有任何一种敬拜音乐应成为一个人灵命塑造的唯一来源 (无论是电子风还是葛利果圣歌) 。基督徒的神学饮食,应该像摄取热量那样,均衡、多元,并由懂得 “属灵营养” 的专家把关。讲道、祷告、查经与其他属灵书籍的阅读,应补足敬拜时较少触及的主题。而我们这些普通会众也应能信任牧者会仔细审视敬拜歌词中的神学。
在网路上那些反对当代基督教音乐的圈子里,批评者常抱怨流行敬拜歌曲背后的事工充满争议的神学及行为——例如伯特利教会激进的灵恩教导、Elevation教会带有成功神学 (昌盛福音) 的味道、或Hillsong爆出的性丑闻与财务管理问题。
然而,这些团队为大众创作的歌曲,通常会避开神学上的差异之处,专注于 “纯粹的基督信仰” 核心。而艺术家或牧者个人的失败,也不会减损歌词本身的神学正统性。愤世嫉俗的人会说,这些人之所以紧抓关于 “白白得来的恩典” 与 “上帝主权” 等基本教义,只是为了触及并在全球最多类型的教会中卖出更多专辑。但我心中不那么愤世嫉俗的部分,则感谢上帝让我每周都能再次被提醒福音最基本却最核心的真理;而归信基督信仰本身,也要求我们脱离盛行于世俗文化的愤世忌俗姿态。文化与政治的潮流不断将基督徒彼此拉远,逼我们为次要议题吵架。当代敬拜歌曲能把我们带回耶稣面前。
我如今在每个主日都满怀感恩地唱着这些歌。我会在车上把音响声开到最大,吵得全家受不了。而如果有一天,这些歌不再使我产生敬畏之心,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翻出我的俄罗斯东正教圣歌CD和《公祷书》。毕竟,要带领及门训像我这样的罪人,需要整个教会的力量。
Molly Worthen是历史学家、记者与教授。她最近的著作是《施咒:魅力如何从清教徒时代到川普时代形塑美国历史》(Spellbound: How Charisma Shaped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Puritans to Donald 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