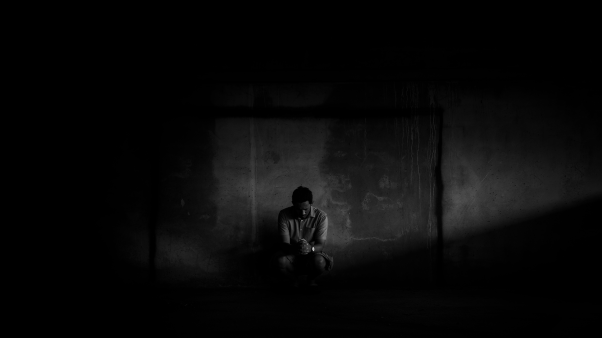保守派基督徒评论家伦恩(Aaron Renn)去年曾写道:“中产阶级和奋斗阶级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他说,中产阶级的目标是“建造一种生活样式”,追求的是“美国梦”里那些物质层面的东西。相比之下,“奋斗阶级者”的目标则是“在世界里往上爬”——虽然经济层面可能是上爬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追求社会上的认可,尤其是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同侪的认可。
伦恩说,中产阶级的志向是拥有一栋不错的房子,并享受愉快的假期;而奋斗阶级者的志向则像是“成为一所优秀大学的终身职教授,或在纽约时尚地段拥有一间公寓,又或者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一篇专栏文章”。
当我读到伦恩这篇贴文时,我心想:啊,这就是我啊。我是个奋斗阶级者。
这个认知并不让我惊讶。我从小由单亲妈妈扶养长大,很早就对社会阶级有意识,尤其在教会中感受最深。小学四年级前,我已开始担心自己的衣服不够“正确”——不是说它们丑、不整洁或不合身,而是某种社交意义上的不合时宜。六年级时,我对我们教会那位拥有博士学位、住在新屋大宅、拥有大片草坪的牧师产生怨怼,觉得他对我母亲有所轻视。
“努力奋斗”并非被动的行为。中学毕业前,我不仅开始意识到大学学费的高昂,也发现了西方经典文学的存在,于是自我指派了两项任务:拿到完美成绩,并阅读我能找到的每一本经典著作。我脑中的画面是,有一天我能理解资深学者提及的每一个精妙典故。我甚至尝试用中古英文原文读乔叟的作品。我那本《坎特伯里故事集》和一本破旧的《咆哮山庄》都是我某次轻度闯入一栋废弃农舍时找到的。
13岁时,我选修法语而不是西班牙语,只因为法语听起来比较高级。毕竟,在我阅读的书中常看到法语的引用。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模糊地想像自己未来可能会当国务卿,成为穿着像凯萨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那样,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中用大西洋口音说话的角色。到了高中后期,我转而决定当调查记者。虽然我最终并没有走上那条路,但我对记者工作的向往,并不全然是因为它可能带来普立兹奖的荣耀——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无关。
成为一个奋斗阶级者,让人生某些失落的时刻格外刺痛。16岁那年,我痛苦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申请耶鲁大学并进入面试阶段后如何功亏一篑。那种痛苦的自觉至今难忘。而这种奋斗的心态也使人容易过度斤斤计较。如今,大学毕业已超过二十年,我最难以启齿、也最不讨喜的一件事,就是我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高中校长是如何不公地阻止我成为毕业致词代表——那个头衔最后落在他儿子身上。
伦恩自己也是一位奋斗阶级者。他今年春天于Substack上一篇文章中扩展他对奋斗阶级的分类时,坦承了这一点,同时也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奋斗本身是件坏事。尽管我以为他会同意每种人生方式都有其特有的陷阱和诱惑,但伦恩仍将中产阶级和奋斗阶级一并描述为“完全正当的”生活方式。
身为一名奋斗阶级者,我很想赞同伦恩的说法。我想要有人告诉我,我这样其实没问题。但伦恩关于“奋斗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行为”的主张,在基督教传统中却远非主流观点。从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的论述,到米洛斯列夫.沃弗(Miroslav Volf)在他新出版的《野心的代价:为了胜过他人而奋斗如何使我们变得更糟》(The Cost of Ambition: How Striving to Be Better Than Others Makes Us Worse)一书中,都主张我们所说的“奋斗”或“野心”,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一种罪。
那么,我的奋斗算哪一种呢?是无害的吗?还是像某种中立的工具,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行恶?只是个人品味和才能的差异?还是如阿奎那所说,是一种“无节制的欲望”,一种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渴求,而不是“为了上帝”或“为了他人的益处”的努力?
我带着这些问题阅读并反思沃弗这本书。这是一本篇幅不长、具有文学气质的作品。沃弗在书中和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及弥尔顿的《失乐园》展开对话,同时引用圣经的见证。沃弗的核心论点在于区分“追求优越”及“追求卓越”。他在书的开头便说明,他关注的不是单纯想要变得更好,而是那种“想要比别人更好”的努力。
这种区分比乍看之下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在一种将人们训练成习惯用数字、名单和排名来思考事情的竞争文化中,任何进步往往会变成一种“相对的进步”,而这种“相对性”是以他人的位置为基准。如果我努力变得更好,按常理我就会变得“比别人好”;如果一支队伍获胜,另一队就会失败;如果我收到耶鲁寄来的厚重信封,就表示有人只能收到单薄的拒信带来的打击。荣耀是有限的,并非人人有份。
但沃弗指出,追求优越“本质上与自我提升无必然关系”。尽管两者经常同时出现,但“我也可能因为他人变差,或刻意阻碍对手的表现,而变得比别人优秀。甚至有可能每个人都变差了,而我依然比所有人优秀。”正如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名言所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安心地统治;对我而言,能够统治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即便得在地狱里;宁为地狱之王,不作天堂之仆。”
这个区分,让“追求优越”及“追求卓越”之间出现一道明显的鸿沟,而《神学大全》中对“罪恶的野心”的定义,正恰如其分地落在这个缝隙之中。阿奎那指出,问题不在于“奋斗”本身,而在于那种为了自身荣耀而奋斗的心——这种荣耀以他人为代价,忽视上帝和邻舍——即使可能包裹在“为了上帝而奋斗”的目标中。
如果我大胆地借用《神学大全》的锐利刀锋重新切入当代语境,那么有罪的就不是我们今日语言中温和意义上的“野心”。它既不是沃弗说的那种“想要变得更好”的奋斗,也不是我和伦恩在职业生涯中所追求的社会或知识地位。有罪的是雅各所说、与狂妄和嫉妒并列的野心(雅各书3:14-16),也是保罗用以与基督形成对比的那种“贪图虚浮的荣耀”(腓立比书2:3-5)。
也许,接下来自然的转向,是开始思考“谦卑”作为与“野心”对立的基督教美德。这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中的论点:“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
然而,使徒在这里的呼召不仅止于谦卑,还包含了对“慷慨”的敦劝:一种坚持要顾念“他人的益处”的态度。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劝勉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祂本有神的形像,与神同等,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像”,受苦、受死,并被上帝升为至高(腓立比书2:4-11)。沃弗是如此评析以上这段经文:
基督并没有紧抓着至高者的特权不放,反而降卑,成为那些最被人轻视的人的仆人。祂没有从他人那里夺取荣耀并据为己有,而是寻求将众人提升,让所有人进入那一切美善及荣耀能共享的荣光之中。这是一种赋权及让生命增长的逻辑,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人;这里不存在比较性的优越,只有对卓越条件的慷慨施予和广泛的分享。
基督的奋斗最终带来了至高的荣耀,但这荣耀是在祂拯救世界的过程中所得。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话来形容保罗——他本人似乎就是个天生的奋斗阶级者。他这样向加拉太人回忆过往:“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加1:14)。他也曾对腓立比教会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3:4-6)
但在归主之后,保罗坚定地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冲劲转而用来服事基督(歌罗西书1:28-29) 和上帝的教会(林前12:31;歌罗西书2:1-2)。保罗因基督的缘故,视过往一切成就为一种损失(腓立比书3:7-10)。没人能否认保罗仍然充满雄心——看看他的宣教地图就知道了——但保罗“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15:20),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
那么,也许我可以稍微释怀。我离效法保罗——更遑论效法基督(林前11:1)——都还差得很远,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在工作中没有为了胜过他人而奋斗。身为作家,当然也会面临各行各业都会有的竞争:争取机会、职位及注意力。但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好的写作,尤其是好的基督教文章,它的成功并非零和游戏。如果有一位更成功的作家能引导读者走向对上帝的忠心及美德,对所有人都是益处,也包括我。如果我也写得很好,也许他的读者会读到我这里来(反之亦然)。我们可以一起促成一个良善的循环,既造就人,也推动出版业。
这并不是说我内心已全然没有对“他人的认可”的渴望。从本质上来说,我的工作需要被看见才能成就。我视自己的主要使命为“劝服人心”,而劝服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性的事——也就是说,我需要读者。若没有人可被说服,那么无论我写得多好,都不能说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就称不上达到“卓越”的成绩。
然而,所谓的“认可”并不是种稀缺资源。我所追求的是“在众人之中变得更好”,而不是“比别人更好”。我并非从来不会对别人的畅销书或订阅人数感到一丝嫉妒,但多数时候我都知道,其他作家应得的赞誉并不会让我有所损失。我也可以坦然无愧地说,我真心为他人优秀的作品能获得应有的肯定而高兴。
即便如此,我也意识到,我如果就这样轻松放过自己,我就错了。
那天,我在为即将到来的半马拉松做训练跑,脑中浮现比赛时我可能会跑出什么样的成绩。我高兴地回想起自己2016年创下的个人最佳纪录,想像着如果我在几乎过了十年、生了三个孩子后,还能跑出一样的成绩,会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当年,我排在女性选手的前10%。如今,在年龄组变老、参赛者更多的情况下,我有没有机会排进个位数?我能比同龄人更优秀到什么程度?跑得更快?训练得更好?穿得更有型?她们会注意到我穿的是那件来自昂贵的新英格兰品牌、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低调运动服吗?她们会欣赏我的品味吗?她们会欣赏我 吗?
那一趟训练跑我表现得很好,但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原本打算在这篇文章里为自己开脱,证明自己渴望奋斗的心是无辜的。沃弗的书也许对你会很有帮助,亲爱的读者们。但我可能不太需要。我已经处理好自己的心态了,或者说,我已经处理得够好了。
但我其实没有。
沃弗在《野心的代价》一书开头,就以运动场上的奋斗作为切入点。事后回想,我当时觉得这个开场有点可笑,而这本身就透露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对我们多数人而言,运动只是个游戏——是一种人为安排,虽然本质上存在竞争,但基本上是人造的竞争。我会在这场比赛中试着超越其他跑者,但不是因为我们在逃命,也不是为了赶去某个目的地。这又不是传说中的第一次马拉松(奔向雅典报捷的生死冲刺)。运动的本质就是运动本身,而跑步彼此竞争就是目的所在。我们当然会奋力一搏!这是无害的。
而我确实认为比赛可以是无害的——如果奋斗是为了追求卓越,如果超越他人只是为了“好好比一场赛”的自然结果,那这种奋斗确实可以是无害的。但我人生的奋斗并不全然是这样。我的奋斗并不都像沃弗所说,是那种纯粹为了真实的美善而努力的奋斗——为着美善本身,为了美善对我、对他人、对世界的益处。我所有的努力,不都单纯以基督的卓越为衡量标准。
我还没有学完人生的这一课,还没完全克服这个毛病,也没什么值得雀跃报告的新的美德。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应该已经跑完比赛了,但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全程毫无一丝关于“比他人好”的念头。尽管如此,也许我可以在奔跑时默想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2-14节中谈论自己如何从罪恶的努力中转向基督时,所展现的真实面和坚持: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还是竭力追求,或许可以抓得住基督耶稣要我抓住的。弟兄们,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我只专注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争取前面的,向着目标直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天上呼召我去得的奖赏。(新汉语译本)
他在第15节补充道:“所以我们当中凡是成熟的人,也要有这样的想法”。求神让我也能如此。我想我大概永远都会是个奋斗阶级者,但我渴望我会为那些不需要向人忏悔的事而奋斗。
Bonnie Kristian本刊思想及书籍部的编辑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