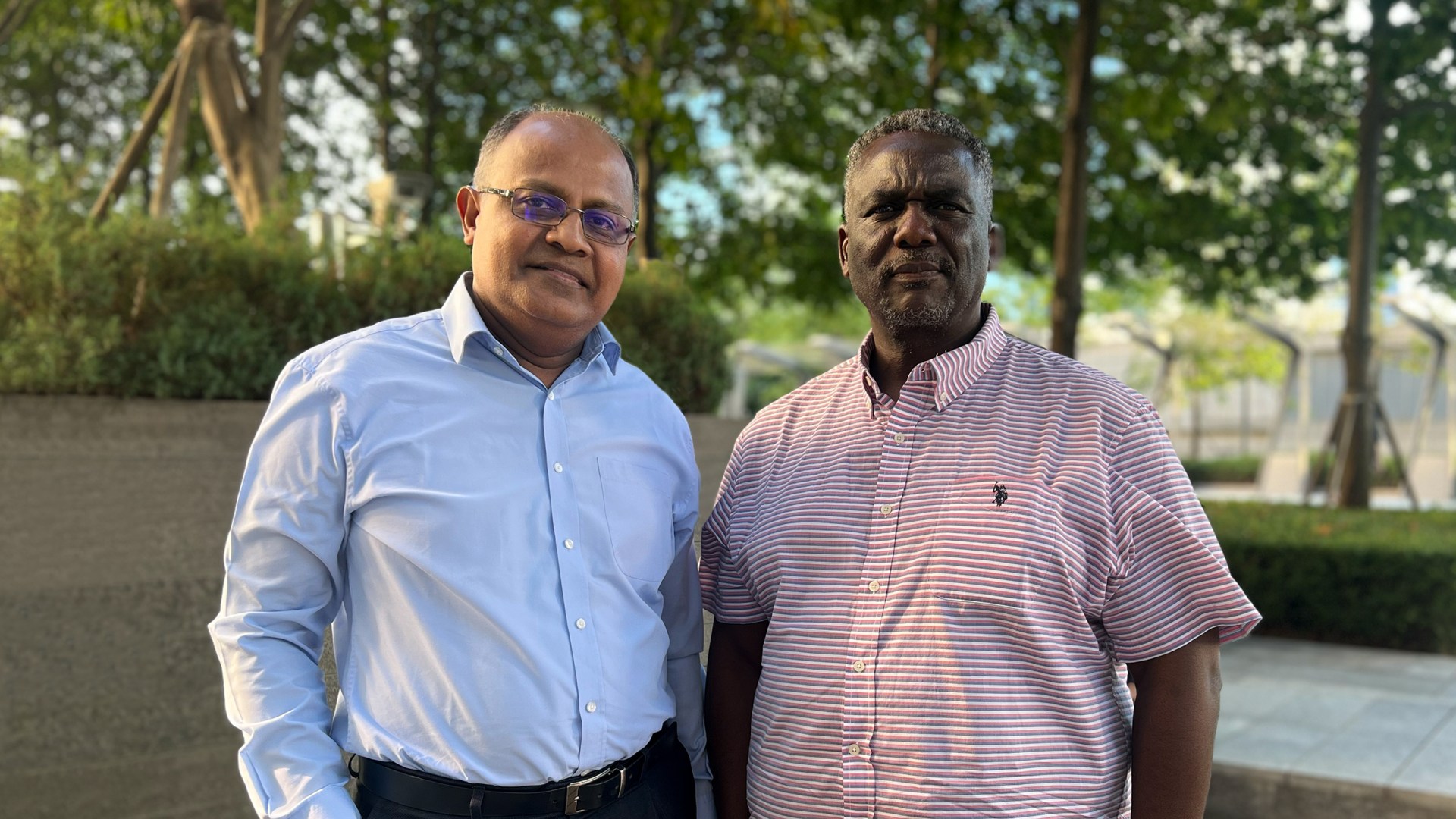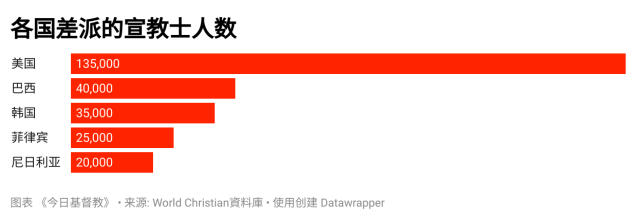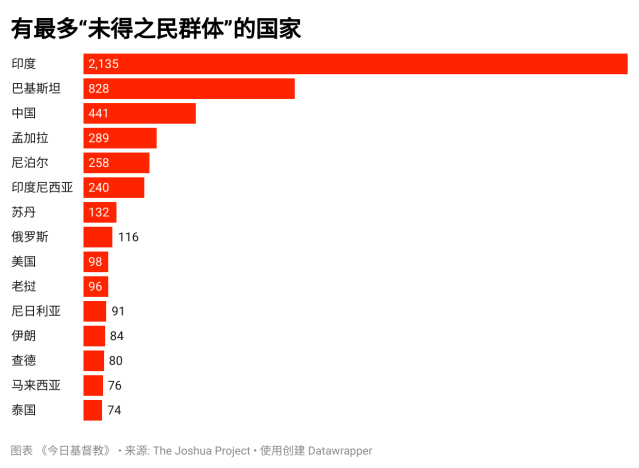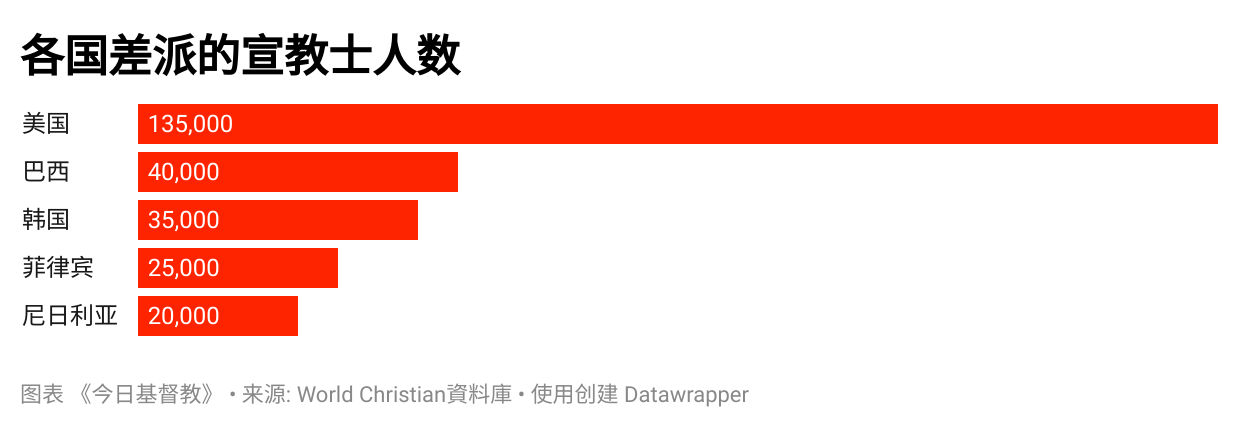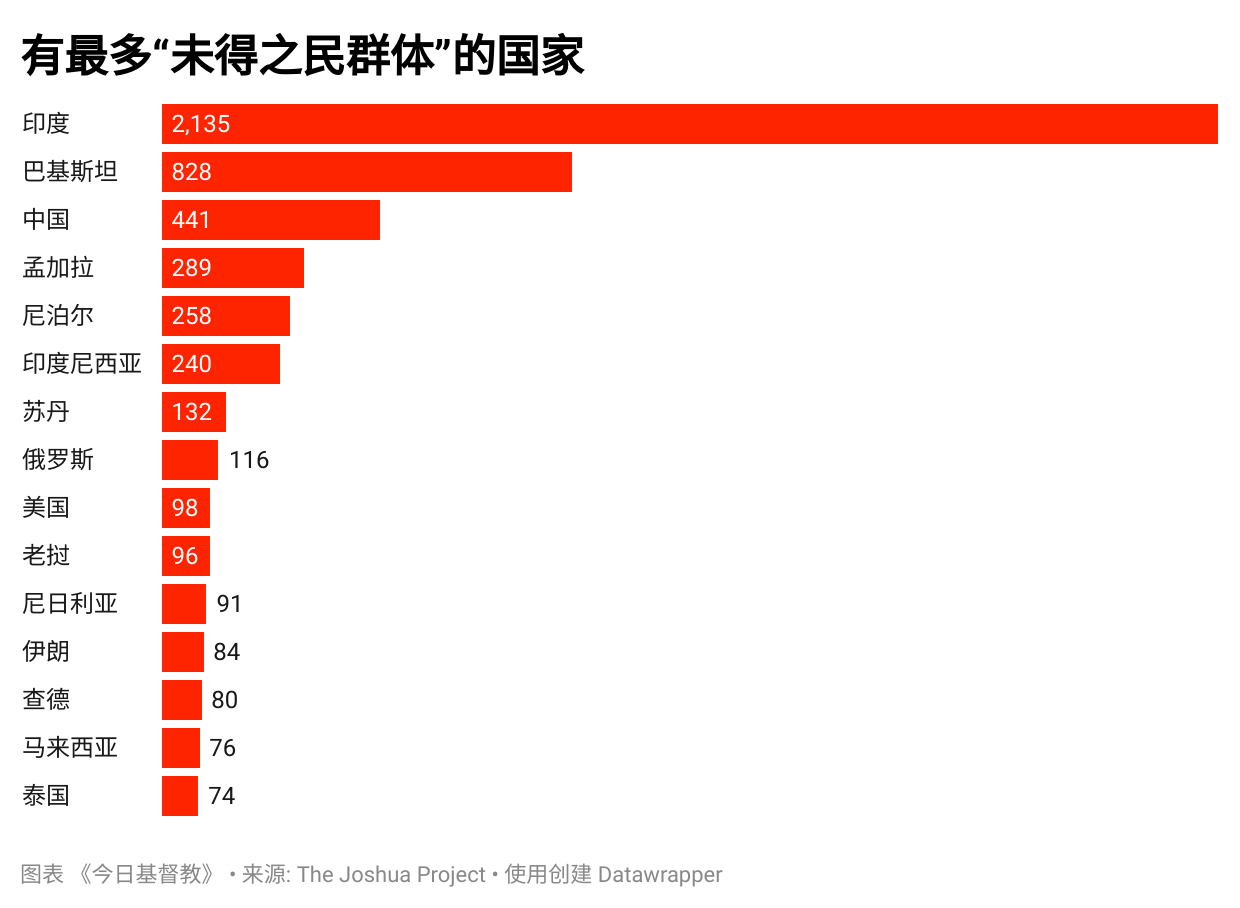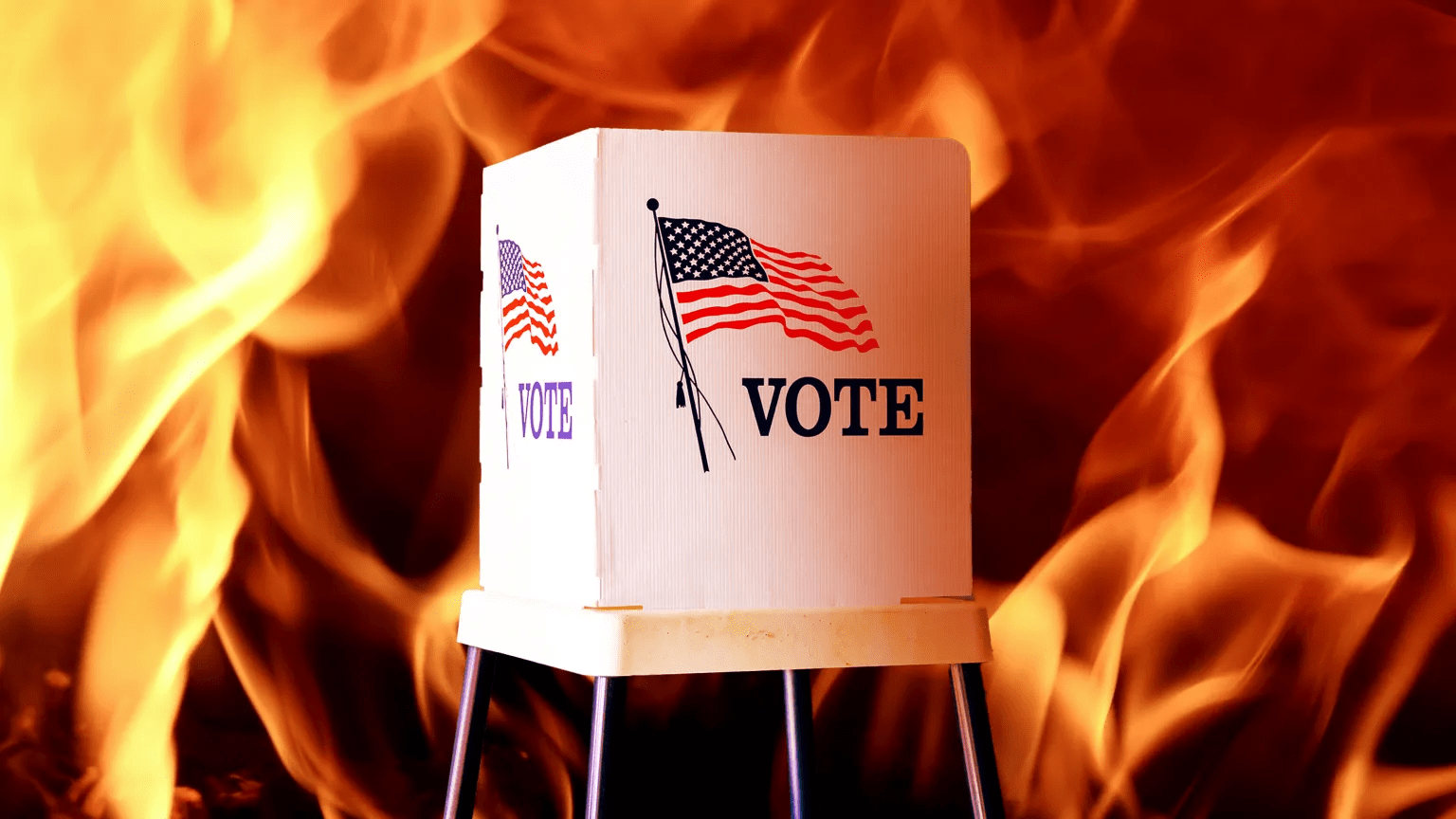如果摩西拿出他的手机拍摄荆棘燃烧的影片,而不是全神贯注看着它,他会错过上帝对他说的话吗?如果马利亚在日常工作的休息时间滑手机,她会不会因为分心而没有注意到天使的到来?
摩西和马利亚见证了永恒打破世俗的那刻,见证奇迹打断平凡日子的时刻。他们完全活在那一刻时间里。
我们能说自己也是这样吗?我们担忧时间的稀少,渴望逃避会“浪费”时间的事物:电视和新闻、手机讯息和电子邮件。讽刺的是,当我们感到无聊或想要分心时,我们却会使用这些科技来加速时间。手机内的影片和照片将我们从全然活在当下时刻的经历里拉出来
试图囤积时间或浪费时间只会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快。就像底部有洞的沙漏一样,时间不断地流失,当我们注意到沙漏几乎流光时,又十分地惊讶。但我们该如何修补沙漏,一粒一粒地恢复时间?
我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六年间,与时间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状态。我既希望它快一点,也希望它慢一点。当我步行、骑脚踏车或搭地铁时,我会疯狂地计算时间。如果我发现自己卡在某处——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或在公车上缓慢移动——我会马上掏出手机,不断地滑动画面、一页又一页,试图逃避时间,希望时间过快一点。我会直接没看到燃烧的荆棘丛,从旁走过,或在被天使打断后低头回去看我的手机。
我与时间的冲突感让我决定做些实验。我热切地尝试操练安息日、静默独处、没有手机的长途散步、以《公祷书》祷告,或禁用社交媒体。但这些尝试永远都不够。这些练习常常让我感觉只是要从塞得太满的日程表中挤出更多时间的另一种要求。而且这些操练多数时候都是单独进行的。无论是工作压力、看Netflix、浏览社群媒体或阅读新闻,生活就像我一个小女子在与整个文化搏斗,一个要求我投注更多时间、更多自我的文化。我拼了命不想落后,跟上步伐,同时还要留出时间给朋友、家人、教会和休息——所有这些也开始让我觉得是种义务。
我读过足够多的书,知道紊乱的时间关系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更是焦虑。但我没有想过信仰群体可以如何在这件事上帮助我。原来,靠我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与时间的关系是不持久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教会的帮助。
我在华盛顿特区时参与的圣公会教会开始了一项新的计画,叫做基督徒灵命培育小组。我第一次读小组的承诺书时,立刻觉得“不可能办到的吧!”。对于像华盛顿这样的城市来说,这些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无法压制内心催促自己参加这个小组的急迫感。
这个为期六周的小组计画包括一长串灵修操练,分别为“脱离”和“依附”而设计,两者相互作用。 “脱离”的练习包括不使用社交媒体、不独自使用影视串流平台(每周允许与其他人一起观看三小时)、不聆听圣经以外和以基督为中心的音乐以外的音讯,以及不阅读圣经之外或符合腓立比书4:8教导之外的书籍。
“依附”的操练则包括每周参加一次灵命小组、每天以降服的姿势祷告30分钟、每天读圣经,每周一次志工服事、每周禁食一次、每周招待“属灵的朋友”一次、每周操练安息日一次、以及一次10小时的退修,并在完成六周计划后的四个月内,每月参加一次灵命小组聚餐。
我立刻被这些操练与“时间”有极大的关联性所打动。 “脱离”的操练鼓励我们减少花在心不在焉的时间上(或什至不花任何时间在这上面)。 “依附”的操练则鼓励我们花更多时间与其他人、与上帝的话语、与圣父、圣子和圣灵交通。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第一周会让我们感到焦虑的问题很简单:当我工作一整天回到家时,我要做什么事?盯着墙看吗?这个计画要求我们事先做好准备,列出可替代的活动清单,以及在我们重新分配的时间内要为哪些人或事物祷告。
Andrew Root在《世俗时代的会众》(The Congregation in a Secular Age)一书中指出,我们现代人对时间的感受有如一种饥荒——不只渴求每天有更多的时间,而是渴求在每个流逝的时刻都有更丰满、更有意义的体验。矽谷要求我们创新、加速、最大化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无止尽地处理多项任务,做得更多、更快。讽刺的是,声称可以节省时间的装置却让我们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我们无法放慢脚步,聆听自己的思绪,更遑论聆听圣灵的低语。
这种狂乱使教会特别难引导会众进入神圣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为了速度,时间被清空了”;教会存在的目的变成“改变人、强迫性的成长”,而不是“在圣灵里的生命转变”。我们需要教会逆着这股“加速的文化”而行,真正成为我们学习操练居住在神圣、神秘和永恒里的地方。
加入这个计画后,时间和我的关系似乎变了。搭地铁的时间变长了,晚上在家的时间变宽裕了,每天早上30分钟的祷告变成一种安慰,而不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一些“脱离”的操练还算容易。但像是背诵经文、志工服务和禁食等依附的操练,却特别难塞入我满满的日程表中。有几个星期,我完全无法容纳这些操练,而禁食不吃饭的饥饿感让我更紧绷。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聆听有声圣经的操练。我做晚饭时听,洗碗时听。渐渐地,我心中的声音改变了。我经历到生命的宁静与和平,而不是混乱与噪音。
“减少消费、接收的来源(娱乐选项)”——只接收“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内容——长期下来累积的效果,是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在搭乘地铁或晚上在家的时光中,我不再向脑海挤进更多内容,而是有片刻的时间静下来与我的思绪共处,并在突然有感时祷告,而如果我在玩手机或看Netflix,我可能会错过这个“突然有感”的时刻。
但真正让这种操练与之前不一样的,是我的属灵群体。在群体聚会的日子里,当我们沉浸在彼此分享的故事里时,时间完全失去了它的结构。我们彼此同理将这些操练付诸实践的困难处,并相互鼓励、并肩努力以新的方式驻足于时间之中。
与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经验——自在地掉泪、欢笑和分享智慧的言语——创造了Root所说的“共鸣”的时刻,正是能解决我们对时间的饥荒感的方法。根据Root的说法,共鸣是种时间的“集结”,充满意义和目的。为了创造共鸣,我们必须跳脱自我,放下手机。在与上帝或与他人相遇的时刻,在这种延伸的时刻里,我们让自己处于敞开的状态、脆弱地接受上帝所命定的恩典时刻。共鸣能将时间沙漏填满,补足我们的灵魂,而不是耗尽我们。
当我与其中一位共同带领灵命小组的牧师谈话时,他说这个小组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简单性——回归到基督教信仰最基础的事物。脱离及依附的节奏,在这个我们被告知要“善用时间”的时代,感觉特别地突兀——因为这种节奏着重于委身而非结果。禁食和祷告并非我们可以立即看到“生产力”的操练。
但事实上,一起聚会、读经、静坐这些基督教历史悠久的简单操练,在每个时代都感觉如此新鲜。在被评为美国最孤独城市的华盛顿特区,我的牧师说,我们也应该视我们的群体/共同体(community)为一种灵修。我们无法以独居个体的方式来重拾神圣的时间,尤其在科技如此强大且让人上瘾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这项任务实在太困难了。
这个逆着文化而行的灵修小组改变了我与时间的关系:时间成为丰富的,而不是稀少的;时间成为ㄧ种机会,而不是负担;时间是与他人共处的,而不是花在自己身上的。正如诗篇90篇提醒我们的,我们必须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并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花费时间,因为“一千年在(上帝)眼中看来,如同一日”(诗篇90: 4)。
在灵修小组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没有独自努力逆着我们的文化而行,而是和别人一起主持周末的静默退修会,并参与每周的聚餐。我委身于每天早晨的祷告和读经,但这次是和朋友一起。在赞美和祷告中一起度过的时间似乎倍增了,也似乎慢了下来。时间变得好多、好充裕,但没有多到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并且我的时间与他人的时间共鸣。燃烧的荆棘闪烁着,我的主在说话。
一个以能将人们带入超然、神圣的时间而闻名的教会,是贪得无厌的消费文化和加速文化真正的喘息之处,是个能吸引人驻足的地方——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Aryana Petrosky是爱丁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的研究生,研究大公修道、灵修和公共场合中的信仰。她协助创办The After Party:Toward Better Christian Politics(迈向更好的基督教政治),并曾在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s Initiative on Faith & Public Life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