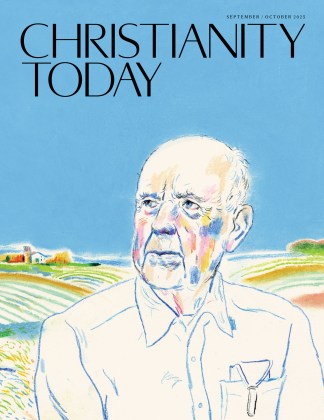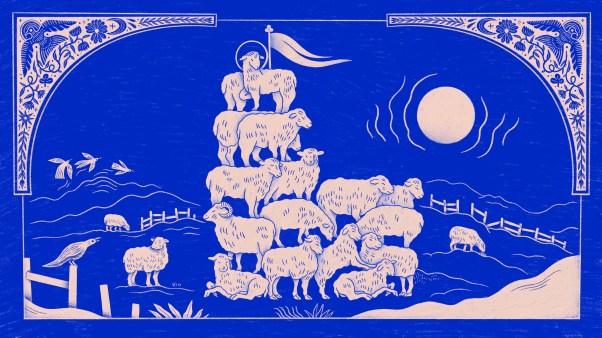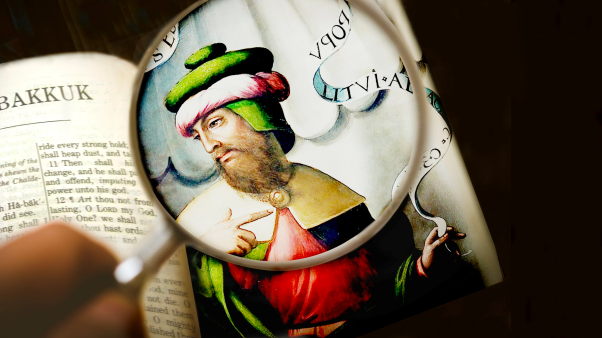我的孩子在学龄前就已接触到一些我直到成年才遇到的事物。举例来说,我的大儿子在5岁时就已熟悉大麻的气味。一次家庭旅行中,当我们经过一名正在抽大麻的青少年时,儿子深吸一口气,说:“啊,闻起来像家的味道。”
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牧师,甚至教授们,都警告我要避开各种败坏的影响:毒品、媒体、某些特定的人,以及危险的思想 (和提出这些思想的作者)。但对我的孩子来说,避开这一切并不在选项中,因为我们住在曼哈顿。他们一定会在街上或地铁里遇到令人不安的人。他们一定会遇见不同语言、宗教,以及各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身为父母,我需要引导孩子去消化这些经验,而不是单纯隔绝它们。
我从最初那种无法替孩子筑起保护罩的状态,逐渐转变成正面迎击地选择让孩子看见世界的复杂性。在必然的处境下,催生了一种价值观:如果我们无法避开住在隔壁的威卡女祭司,那么我们就不该避开住在隔壁的威卡女祭司。最后,我什至开始对那些刻意把孩子与 “现实” 隔绝开来的父母,产生一种自以为义的批判态度。
所以,当我们从曼哈顿搬到凤凰城时,你可以想像我有多惊讶。才搬来几天,当我带孩子去郊区的一间超市时,门口有人在乞讨。没多想之下,我带着孩子绕到另一个入口。我避开了一个在纽约时的我绝不会回避的互动——因为现在 “我有办法避开”,我就本能地避开了。在新的处境下,我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能避开Target超市门口的乞讨者,那么我们就应该避开Target门口的乞讨者。
在阅读布米勒 (Brian Miller) 的《将郊区神圣化:郊区如何成为美国福音派的应许之地》一书时,我开始思考:这种倾向于回避那些在身体、心理或灵性上看似有危害的事物,是一种郊区心态,还是一种“基督徒心态”?米勒身为惠顿学院的社会学家,视这种本能为 “郊区文化工具箱” 中的一件工具,被福音派 “施洗” 后,纳入我们自己的文化工具箱。他的书提出一个颇为合理的论点:许多我们以为独属于福音派的思维,其实起源于郊区。
随着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变得更宗教化,美国同时也变得更 “郊区化”。根据《全国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长达45年的数据推估,福音派比其他群体更倾向居住在郊区。事实上,福音派进驻郊区的比例甚至高于一般人口。而那些塑造了福音派在社会、政治与神学上的参与的关键机构——包括米勒任教的学校——几乎全都设立在郊区。
在这一切背景下,如果 “郊区心态” 没有影响福音派的信仰与实践,才会令人感到意外。正如米勒所主张的:“研究人员和评论者,若只考量福音派的神学立场与政治行为是不够的;要理解白人福音派的整体样貌,理解他们所处的空间脉络 (spatial context)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追溯美国郊区的起源与历史后,米勒提出引人入胜的质性资料来支持他的论点。他追踪了20世纪芝加哥及其郊区的宗教迁移情况,发现 “在1925到1990年之间,所研究的10个新教宗派中有9个宗派的教会变得更加郊区化”。透过绘制全美福音派协会 (NAE) 重要领袖的住址分布图,他也发现来自郊区的领袖代表在数十年间显著上升。在该组织1942年的首次董事会议中,仅有15%的代表来自郊区;到了世纪末,这一比例已成长至一半。
米勒综合多个来源的数据,指出在美国城市整体变得 “较不宗教化” 的同时,“在更偏乡和最小型社区中的基督徒比例 [同样] 在下降,特别是福音派和主流新教基督徒的数量”。福音派正持续变得更不都会、更不乡村,以及愈来愈郊区化。
米勒也描绘了三个郊区与一个小城市的案例,这些地方的福音派及其相关机构具有异常突出的影响力。这些社区分别在不同年代、不同条件下郊区化。其中两个社区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福音派身份认同,另两个则是在近年才成为福音派的热点。综合起来,这四个地区汇聚了数千个福音派非营利组织,因此能在更广泛的福音派群体中发挥超过其规模所应有的影响力。
当米勒谈到 “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 时,这些数据的意涵就更耐人寻味。在社会学里,“工具箱” 的概念用来描述文化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文化并非单纯提供一套价值观,而是提供一系列行为的 “工具库”,让个体可以从中选择不同的行动路径。
那些渴望推动社会改变的人,手上各有不同的文化工具可运用。他们可能选择在 “人际关系” 的脉络中说服他人,也可能选择组织行动,推动法律与公共政策的改革。而文化会影响人们何时认为该采用哪一种工具。例如,历史上,福音派基督徒面对种族不公时,往往采取人际关系的方式;但在抵制同性婚姻时,则倾向采取立法行动。
米勒的核心观点是:“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似乎是依据 “郊区生活” 中常见的模式、经验与愿景调整而来的。他谨慎地避免断言 “郊区规则” 与 “福音派特色” 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指出其中的动机、方式与机会之间的连结。
接受 “较狭义” 的米勒论点应该不困难:郊区福音派是在 “日常生活的规律片刻,以及与美国郊区社会和物质实况的互动中” 中所形塑的。但对许多人而言,要接受 “美国福音派整体在本质上就是郊区化的,其价值观与心态深受郊区影响” 会比较困难。
这正是为什么米勒对 “福音派热点”(evangelical hot spots) 的分析对我来说特别切题。如果大部分的福音派机构——大专院校、神学院、宗派总部、出版公司、植堂与宣教机构、课程公司等等——都位于郊区,那他们的员工很可能也住在郊区或附近。
这意味着,福音派基督徒的课程设计、研究问题与教学大纲,都可能受郊区师生所感受到的“需要” 与 “兴趣” 所塑造。出版商在掌握福音派读者的脉动时,或许也会自然地以郊区经验作为市场需求的基准。大型郊区教会经常成为教会课程、门徒训练方法与牧养 “最佳实践” 的范本。而关于教养子女、个人理财之类的建议,往往预设 “郊区的社会现实” 是普世适用的常态 (norm)。
总体而言,米勒认为,这些机构将一种根本上属于 “郊区” 的视野,包装并处方为一种 “客观上的基督徒视野”,进而引导福音派在所有环境下的信仰与实践。对我而言,这一点并不牵强。我的事工经验与专业工作,主要涉及乡村与都会的教会。这些地方的牧师常哀叹,他们所依赖的资源,明显是根据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社会现实所设计的。至少可以这么说:美国的事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郊区经验” 所主导的。
《将郊区神圣化》是一部细致严谨的学术著作。它避免了对郊区的刻板印象,并承认郊区在历史、人口与宗教身份上的多样性。它也提出一些明显超出书本范围、需要其他学者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涉及 “种族”。米勒将 “福音派新教徒” 与 “白人福音派” 视为同义词。将 “(白人) 福音派新教徒” 与 “黑人新教徒” 区分开来,使米勒能比较宗教与人口学的数据。这种做法很有帮助,因为它能具体指出:第一个群体比第二个群体在更大规模上逃离芝加哥并移居郊区,也显示 “白人外移潮” 促成了郊区更具福音派色彩的现象。
然而,将 “白人” 与 “福音派” 划上等号,对于解释亚裔与拉丁裔福音派在这个故事中的角色 (无论在历史脉络还是未来发展) 就显得力道不足。非白人福音派的人数正在增加,而郊区本身也日益多元化 (当然,并非所有美国郊区皆如此)。我很好奇,在这个更广泛的种族意义下,“种族因素” 将如何影响郊区与福音派的文化工具箱。
关于阶级,我也有类似的疑问。我们在曼哈顿的经验显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替孩子筑起保护罩。那么,郊区圈内的经济差异又将如何影响主导性的文化工具箱?
另一个问题则涉及福音派郊区化的 “完整范围”。更深入的历史检视,也许会揭示郊区经验对福音派的影响超越郊区的界限。例如,米勒的历史回顾回溯到18世纪的伦敦,用以说明 “人们对郊区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迁入郊区的宗教动机。”
伦敦西南部的克拉珀姆 (Clapham) 郊区,在18、19世纪是 “克拉珀姆教派” (Clapham Sect) 的所在地。这群福音派圣公会成员包括推动废奴法案的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以及其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改革者 (这是文化工具箱中的一项);他们也把家庭迁往郊区,以避免工业化后都市生活所带来的 “腐蚀效应” (这又是工具箱中的另一种工具)。普莱尔 (Karen Swallow Prior) 在《福音派的想像力》中有力地指出,当代美国福音派的价值观,其实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价值观的悠长阴影。而这些价值观,很可能最初就起源于伦敦郊区,之后再被输出到世界各地。
美国福音派一直都是一个多元的运动。无论我们尝试阐述大家的共同点 (如David Bebbington提出著名的 “四边形” 理论),或我们之间的分歧 (如Michael Graham提出的《福音派的六种分裂》),福音派往往专注于明确的信念与价值。米勒的社会学取径,为这些分类带来了急需的深度与维度。例如,我怀疑那些认为社会公义 (social justice) “对福音造成威胁” 的福音派,与那些视社会公义为 “福音本身的使命” 的福音派,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社区。若要理解为何福音派会在社会与神学的根本议题上出现分裂,未来的研究应该效法米勒的路径,去追问:这些人住在哪里?这样的居住处境对他们带来哪些影响?
当英国国会下议院在德军空袭中被摧毁,需要重建时,邱吉尔坚持新建筑要保留原本的格局。他认为,空间的配置会决定其中发生的治理型态。他曾说:“我们塑造了建筑,之后建筑又塑造了我们。”
美国福音派世世代代都高声宣称,要积极塑造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但或许现在是时候,更批判性地思考:那些环境又是如何塑造了我们。
Brandon J. O’Brien,是 “Redeemer City to City” 事工的全球思想领导资深主任,曾与Randy Richards合着《用西方眼光误读圣经》(Misreading Scripture with Western Eyes)。他与家人现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