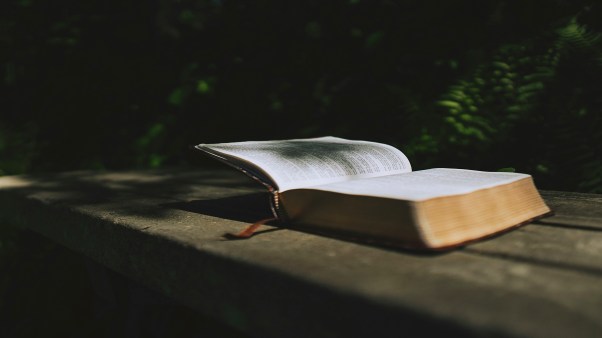美国如今正面临着 “大离教运动” (Dechurching movement) 的风潮。宗教滥权、人心冷漠、数位媒体的操纵⋯⋯等皆被指名为祸端。这场关于离教现象的讨论产生了许多假设,也伴随着许多不太可行的解方。但多数对福音派离教现象的分析,都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教会所教导并以身示范给会众的,是ㄧ种毫无生气的教会神学 (church theology)。也许,那个呼唤人离开教会的声音,其实正来自教会内部。
丹尼尔·威廉斯 (Daniel Williams) 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上撰文指出,许多福音派知名领袖自己就很少稳定参加教会聚会,这种行为反映出他们本身薄弱的教会论。但威廉斯认为,今天的离教问题,不只是因为这些领袖树立了不良的榜样,而是源于福音派信仰深层的一项假设:基督徒的生命最终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旅程,是一场个人灵魂与上帝一起的冒险。
在福音派的圈子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教会经常被视为基督徒生活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只是帮助我们活出个人信仰的一种方式,是促进个人成长或拥有灵性经验的工具。然而这种想法并不正确,严重错失了重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正是基督信仰生命的本质。
因此,试图透过强调 “教会对个人的实际益处” 来解决离教危机,其实等同于试图用导致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诸个人经验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起初开始,罪的本质就是分裂与分离,使一个群体变成彼此孤立的个体——而上帝的医治不可能以疾病的形式出现。
正如洛芬克 (Gerhard Lohfink) 所言,上帝所建造的是一个“民族” ,而不只是一些彼此无关的个体。“成为神的子民” 意味着在祷告、敬虔的生活方式及共同的使命中一同存在,彼此不可分割。圣经吩咐我们聚集,正因为这是上帝呼召我们的方式,也是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的 “新的民族”:在万民中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如同一座圣殿,由一块块的活石联结而成 (希伯来书10:25;以弗所书2:21)。
那么,教会该如何重拾作为 “上帝子民” 的身份?我们该如何挽救福音派的教会论?
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的《团契生活》正是在教会面临一场危机时写的。当时,潘霍华正在帮助羽翼未丰的认信教会 (Confession Church) 建立一所新的神学院。认信教会是因不认同德国国家教会 (German National Church) 的信念而创立的,因为德国国家教会修改了自己的信条,加入一条新条款,以表示效忠元首 (希特勒)。
德国国家教会试图透过将自己与希特勒连结在一起,来展现自己是个真正的 “人民的教会”——这当然是种谋求长期生存的策略,但却付上成为异端的代价。尽管潘霍华处在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时空背景,但今天的教会在今日文化中求生存所面临的挑战,趋使我们问和潘霍华同样的问题:我们试图拯救的 “教会” 究竟是什么?
潘霍华写道,教会并非以个人的经历为中心,也不是以一位能描绘 “令人信服的愿景” 的强大领袖的能力为中心。这些因素也许能让教会暂时运作,但无法长久。相反地,教会一切的实践,都应该展现出一个共同体/群体 (community) 的生命—— 是一群在彼此的相交中、借着彼此,一同遇见基督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彼此相邻而独立生活的个人。
这个群体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因为基督亲自在他们当中。基督呼召每个人超越自我,进入这个共同的身体。唯有靠着基督,教会才能存活并成就使命;也唯有基督,能呼召一群在这世上以 “成为属上帝的子民” 为核心的人,一同成为一个身体。
但如果我们读潘霍华,是为了透过 “建立教会成为一个共同体” 的方式来让教会 “变得更成功” ,我们就误解了潘霍华的重点:是 “身为一个共同体” 的本质,使教会成为真正的教会。
对潘霍华而言,个人独自过 “基督徒生活” 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已将我们连结成一个身体,我们透过彼此对话、共享爱宴、一同阅读并实践圣经的基督徒生活中,与基督相遇。潘霍华在《团契生活》中所推荐的各种操练,与其说是为了使教会成功,不如说是为了使教会成为真正的 “共同体/群体”。
然而,“成为上帝子民” 这个任务,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开始一套新的事工方式,而是要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基督徒生活操练——会众一同唱诗、一同读经、一同用餐——只是这一次,我们心里有个更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群体。正因如此,《团契生活》虽然看似实用的著作,却是一部深邃的神学著作。
例如,当我们一起读经时,潘霍华建议选读较长的经文段落,让经文提醒我们上帝在祂子民中持续的作为,也就是现代教会也要承担的工作。这些经文提醒我们与历世历代基督徒共享的 “老故事” ,而不是单单聚焦在我们个人的处境上。潘霍华尤其推荐诗篇——这本以色列人的祷告书——因为诗篇引导我们思考教会与以色列的延续关系,以及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 “新的民族” 的身份。
同样的,当我们唱诗时,潘霍华建议大家一同开口歌唱,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上,而是让同声敬拜来提醒我们:上帝已经使我们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共同体;当我们一起祷告时,潘霍华鼓励我们先为那些与群体共同面对的事情祈求,而不是立刻转向仅属于个人需要的祷告。
在一周的其他时间里,当我们分散各处,我们仍然有许多其他机会,让基督透过圣经对我们的个人生命与处境说话。但即使在这些时刻,潘霍华也提醒我们,这些 “领受” 的目的,仍是为了建造更大的身体,使我们能将在独处时从基督那里得着的一切,带回教会,彼此分享。
同样的精神也应当贯穿我们如何读经、如何共餐、如何理解宣教。如果教会各种实践及计划的目标,是为了将我们凝聚成为上帝子民,那么不仅我们 “做什么” 事很重要,我们 “如何去做” 也同样重要。
正如潘霍华提醒我们: “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关系,并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实现』的理想,它乃是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现实。我们被邀请去参与其中。” 祷告、唱诗与服事的操练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上帝发出的邀请,邀我们进入基督已然成就的、更深层的真实之中。
我们邀请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 (不只是那些特别能读书的菁英) 都能成为一个 “读经的人”;我们以 “所有人” 都能加入的时间和方式一同用餐;我们宣教、参与事工,不是为了让人变成附属于某个宗教的个体,而是为了使他真的成为一个共同体/群体的成员——在这个群体中,人们彼此发挥恩赐,并从彼此身上领受基督的话语。
在谈论祷告的互惠性时,潘霍华指出,是 “其他所有人在为某个人和他的祷告代求”,使某个人 “为群体祷告” 成为了可能。他问道:“一个人怎能独自为团契祷告,而不倚靠团契的代祷来扶持并坚固他?”
ㄧ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属灵生命,首先倚靠的是上帝在基督里创造的共同体/群体。这里所说的教会,不是一种事后的附加选项,而是整个信仰生活的前提。上帝创造的,是一个新的民族,一个因紧密连结于基督,使其中每ㄧ个人能走进世界的民族。
圣灵将我们从世界各地召聚在一起,也与我们一同走进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我们是否实际聚集在一处。但这种 “走出去/分离” 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被带回同一处。我们本应是个生命彼此交织的民族,而不是一群各自为政、仅凭己力过活的人。
如果我们要真正回应离教的现象,就不能再用那些导致此现象发生的方式来解决它。因为教会给予我们的,是无法被归类在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东西:教会给我们的是耶稣,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唯有在这个身体里,我们才成为基督徒,才经历基督的同在,并在其中被改变生命。
正如门徒们一起学习聆听耶稣的声音,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仅仅修补 “错误的福音派教会论” ,视教会为支持信仰生活的附加工具;事实上,我们必须完全舍弃这样的想法。如果离教现象所抛弃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教会观,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迈尔斯·沃恩兹(Myles Werntz)是《从孤立到群体:基督徒团契生活的新愿景》一书的作者。他为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部落格的撰文作者之一,并在艾柏林基督教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