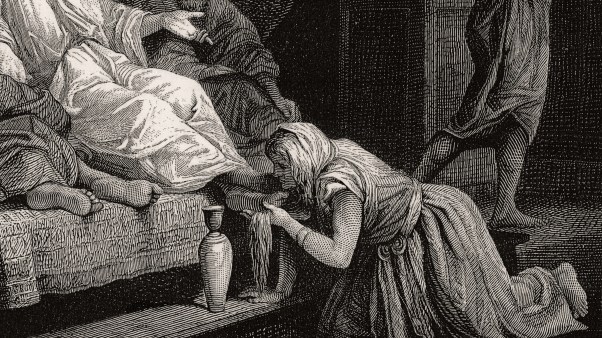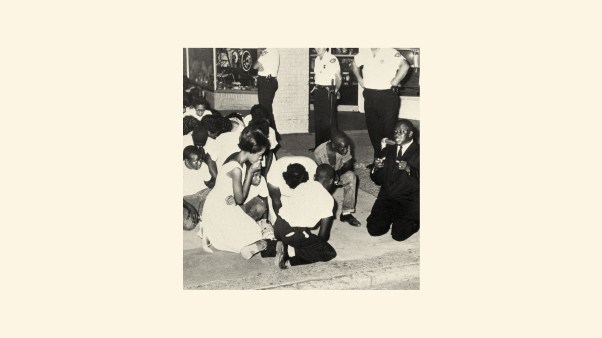几年前,我开始越来越常听到有人说:“推特上发生的事,正在成为这世界的真貌。”
他们的意思是,这个社交媒体app上的有毒争论,正在定义整个时代——影响并塑造人们彼此沟通的方式,从学校董事会会议,到总统玫瑰园的记者会,再到教会的事工会议,无一幸免。
然而,如果 “推特时代正在结束,我们文化的下个时代将由抖音 (或任何短视频平台) 来定义” 呢?这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这个问题在我心中盘旋了好几周,起因是我意外听到有人对美国民主的未来提出一个相对乐观的看法。但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看法的基础竟然是:抖音/短视频。
在《以斯拉·克莱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 的一集中,《纽约时报》记者克莱因和电视评论员海斯 (Chris Hayes) 讨论今年夏天早些时候,社会主义者曼达尼 (Zohran Mamdani) 在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州长古莫 (Andrew Cuomo) 的事。这段对话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当两人开始取笑古莫尝试抖音技巧的场面。
事实上,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跳脱古莫本人,转而谈论许多民选官员与候选人在抖音上尴尬跳舞所造成的 “社死” 感,官员每一次的尝试都证明他们与这种 (和选民的) 沟通方式格格不入。
克莱因与海斯推测,如果要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曼达尼的胜利,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也不是他的 “反以色列” 外交立场,而是他 “达到胜选的方式”:曼达尼似乎是美国大型选举上,第一位能自然地用抖音和Instagram短视频来沟通的候选人。
“我实在不想过度引用麦克鲁汉 (Marshall McLuhan) 的理论,说什么媒介就是讯息、人人都被自己所使用的媒介塑造⋯⋯因为很明显地,在抖音或短视频平台上,很多人并不像曼达尼那样深暗操作法则,或什至根本不知道我说的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 克莱因说。
尽管如此,克莱因指出,我们仍应关注社交媒体平台的演变,是如何加快美国政治生活中所谓 ‘氛围转变’(vibe shift) 的速度。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克莱因举例,奥巴马其实就很不擅长使用推特。这并不是说奥巴马在数位沟通上很笨拙——事实上,奥巴马可能是第一位真正有效运用这些媒介来动员并维持支持群体的政治人物。但奥巴马并不是推特的 “原生物种”,克莱因说:
随着民粹右派的兴起,以及程度稍轻的民粹左派政治在全球各地同时冒出来——这个集中爆发的时期始于2000年代末或2010年代初,我认为导致这种现象其中最强大的驱动力,不仅仅与移民问题有关,也不是经济因素导致的 (从数据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我认为,关键力量是 “核心政治沟通平台” 的兴起,而这些平台的特征是以高冲突、高互动,以及精简的文字为主要表达方式。
“这些平台,在意的是 ‘群体’,” 克莱因表示。“平台关注的是一个群体内部,以及此群体和其他群体的互动;平台在意的是以极其精细地方式划分群体间的分界线;平台的本质使其孕育出更民粹化的政治形式,或至少会创造一种政治沟通的结构,使外来的民粹派政治人物更容易茁壮成长。”
你不需要完全认同克莱因的论点,也能看出他所描述的轮廓——甚至在教会中亦是如此。
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讲道者,或一名成功的布道家,所需的能力与在推特 (现为X) 上吸引追随者来获得 “影响力” 的能力完全不同。推特 (或Threads等短文字平台) 无法承载深思熟虑或深度的论述、交流方式,只能依靠 “钓鱼” 式的冲击战术——挖掘越来越极端的立场,并以激起愤怒或恐惧的方式大量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敌人” 与 “朋友” 一样,都是能放大影响力的有用工具。
然而克莱因认为,像这样的科技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就像2000年代中期兴起的脸书时代,那种 “希望及改变将使我们团结” 的氛围,最终消散了——短视频平台上的暴戾氛围也会如此。
“接下来的时代——你看看抖音、再看看Instagram短视频——我并不是说高冲突的政治内容会消失,而是其中的内容已开始更多是关于日常生活事物,” 他说,“而且是非常高度视觉化的。”
克莱因在一些新一代的年轻政治领袖身上观察到,他们使用的 “语言” 不再是推特的语言,而是抖音的语言。海斯承认:“对,就是那种有趣、带点搞笑耍蠢的沟通方式。”
让我们先暂时不定论这个现象是真还是假、好还是坏。先问问:这些政治人物 “试图呈现” 的是什么?——走上街头,与人交谈并聆听他们的声音。
如果这种现象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风格,会不会塑造一种新文化?也许会。这会不会与在推特/社交媒体上策划激起人们愤怒情绪的文化不同?也有可能。但文化生态中冲突的减少、视觉表演的增加,是否就必然对民主有益?答案是否定的。
哲学家巴尔巴-凯 (Antón Barba-Kay) 在《刺猬评论》(Hedgehog Review) 中指出与克莱因相似的论点——有种转变正在发生,他称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为 “抖音治国” (TikTokracy)。在这样的文化中,民主不再根植于公民教育或理性辩论,而是取决于谁能在演算法的注意力争夺战中胜出——但这仍是推特文化的一种延伸,而不是逆转。
对巴尔巴-凯而言,这不只是政治问题。失去 “阅读及理解” 较长篇的论述,并以此来说服他人的能力,动摇了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存在的根基。更别说,我们甚至还没讨论另一个大问题:究竟是哪一小群科技创业家、国际大势力、企业或政府在控制这些攫取我们注意力的演算法?
帮助人们重新学会 “专注” 的第一步,就是视他们为 “有能力专注的人”。政客或许需要学会如何 “占领” 短影音的领域,但那是因为政客仅仅是在回应又一次的文化变迁、迎合被这一波文化塑造出来的人。
然而,教会有责任塑造门徒——为他们的未来,以及他们所能影响的人的未来作准备。
在这个意义上,教会的呼召并不是要设法掌握所谓 “抖音的语言” ,或掌握下一个取而代之的平台的语法;而是要真正意识到,我们身处的文化语言正在塑造我们、形塑我们、“门训” 我们,甚至影响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不仅仅需要为有疑问的慕道者提供答案 (即使这依然很重要)——我们更需要的是,建立一种带领、以身作榜样,及内在文化的方式,作为 “逆着演算法而行” 的力量。我们需要听到圣经不断大声说出的那句:“耶和华如此说” ,也需要耶稣教导我们的:“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路加福音8:18) 。
耶稣对我们说过的许多话都是逆着文化而行的。面对未来的年代,祂所说的最难做到的教导之ㄧ,可能正是我们许多人忽略的提醒:留心你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何处上。
罗素·摩尔 (Russell Moore) 是本刊总编辑,领导本刊的公共神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