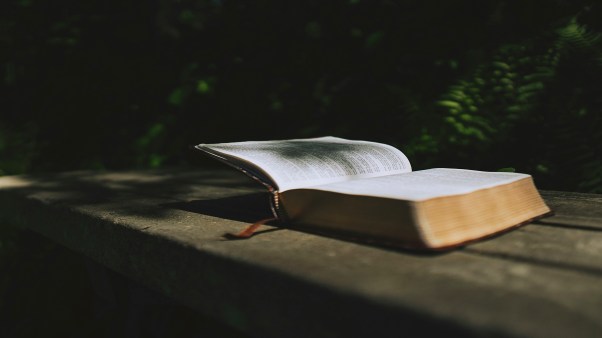我震惊地站在超市的谷物麦片区。在我左右两边的货架上,有数不清种类的早餐谷物麦片,一排排地延伸开来:富含维他命!加上超多棉花糖!有机小麦胚芽制的肉桂脆片,提供你每天所需纤维的两倍!
过去的四年半里,我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在那里,我只能在住家附近的当地食品摊贩街上买到食物。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经过装在大桶里扭动的鳗鱼、小巧银色推车里冒着热气的饺子,以及堆在折叠桌上的一捆捆带泥的白菜。我只能买能装进袋子、徒步带回家的东西。现在我搬回了美国,马上被地方超市店内满满过量的商品所震慑。
在一个物质富庶的地方禁食是件很奇怪的事。这不仅因为我们许多人未曾因 “必要” 而禁食,也因为我们潜在的文化假设。
一方面而言,我们纵容享乐主义:我们的身体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我们把欲望奉为最高的价值,屈服于每种欲望的引导,让它奴役我们。通常,我们已预设快乐为 “拥有多于所需的东西”。就像串流媒体鼓励我们无限地追剧、听歌,智慧型手机以让人上瘾而设计那样,我们所吃的东西也经过精确的设计安排,让我们成瘾。当我们对食物的欲忘被从过量生产中获利的全球食品集团操控时,我们很难正确的调节我们的食欲。
另一方面,我们接受了一种现代诺斯底主义的变体。在柏拉图主义和二元论哲学的强烈影响下,我们将身体与灵魂分开,形成错误的二分法。我们高举非物质领域,认为它比肉身更加纯净、更加真实。而肉身往往被我们视为肮脏、甚至是有罪的。我们会因模仿网红们而过度节食。对许多人而言,“禁食” 往往带着对身体的羞耻感和宗教上自以为义的包袱,可能会刺激到那些在饮食失调问题上挣扎的人。
如果这些谎言仅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也就罢了,但可悲的是,它们也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教会中。
举例来说,教会中的物质主义或享乐主义文化,表现的形式可能为 “不断追求更高的出席率和更大的预算” 以购买更好的设施。我曾有位宣教士朋友,走进我聚会的大型教会会堂时,感到非常愤怒。他环顾我们闪闪发光的萤幕、舒适的座位和华丽的花卉布置后说:“在我们宣教地建立的教会里,我们甚至必须为买折叠椅而募款。我们已在地下室聚会20多年了——这ㄧ切向人们所传递的,是什么样的 ‘基督的十字架’ ?”
教会有时 (或许是无意的) 这样暗示人们:“我们的肉体是问题所在,只有灵魂才是真正重要的”。例如,批评服用抗忧郁药物的基督徒缺乏信心;或除非能确保 “福音会因此传扬出去”,否则教会长老们会拒绝资助海外挖井的宣教行动。这种教会版本的诺斯底主义认为身体有着种种问题,或至少比他们所谓的 “灵魂” 还次等 (认为拯救灵魂胜过服事人身体的需要)。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谬误——将我们引向过度重视或忽视身体——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习惯。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禁食” 作为一种属灵操练,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第三条道路,向我们最常见的 (关于身体的) 谎言诉说真理。
自从多年前偶然接触圣公会以来,我在大斋期期间曾有创意地 “禁戒” 一些事物:不浏览Instagram、停止教会聚会、下午五点后不使用手机。有一年大斋期,我什至禁止自己在与人对话时发出不必要的评论。作为个人主义者,我们喜欢创造量身定制的 “禁食” 项目。虽然这些操练无疑可以在我们与上帝同行的生活里发挥有益的作用,但我还是常常回归在基督徒群体中共同的禁食操练——因为这挑战了我们文化中的谎言。
禁食一直被认为是基督徒的传统,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有禁食的传统。在约翰·科默 (John Mark Comer) 的一集播客里,一位来自伊索比亚的来宾描述在成长过程中,她如何在基督教群体里连续禁食50天 (日出到日落之间禁食)。另一位来宾则喜乐地形容,通常在禁食的第14天,他会对圣灵有更敏锐的感知。
这些经历听起来很棒,但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对于禁食,我还是个初学者,还在摸索如何有规律地在祷告中不吃三餐。在我尝试操练禁食的同时,我也想向其他人学习禁食操练的属灵目的。
十九世纪的宣教士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从山西的中国基督徒身上学到许多关于禁食的功课。戴德生观察到:
由于禁食会让人感到软弱和穷困,它确实是上帝所设立的恩典的手段。也许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阻碍是我们自以为有的力量。而在禁食中,我们体会到自己是多么贫乏、软弱的受造物,依赖一顿饭菜来获取我们所倚靠的一丁点力量。
似乎,上帝喜爱填补我们在禁食中显露出来的软弱。
我也发现在饮食中的自我舍去,可以锻炼我们在属灵征战中需要的肌肉。正如罗伯·莫尔(Robert Moll) 所说:“舍己的习惯能加强我们背十字架的能力,因为我们连身体都一起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 我注意到我在禁食期间,能更坚强地抵抗我个人的软弱及试探。这让我想起大学时期,我会在健身房做腿部重量训练,以便在足球场上跑得更快、踢得更有力。
甚至连耶稣也经历了透过身体的禁欲来获得属灵的力量。在圣灵的引导下,祂禁食了40天,沐浴在天父的肯定中,准备好在旷野中迎战魔鬼。
禁食也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的不良饮食习惯。我们许多人会一边看电视节目一边独自吃晚餐,或在一个又一个忙碌的行程之间抓空档吃速食。我们过度放纵,浪费了许多食物。对于我过去吃了太多的,以及没有吃完的食物,我深感抱歉。
毕竟,即便我发誓戒掉过度饮食,却看着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依然饿着肚子,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禁食不仅是为了让我的身体和灵魂在上帝面前得到正确的调整,更是为了促进我所在的社区实践公义——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我们的贪酒好食和不健康的自我伤害,都发生在现今这个充满真实饥饿的时代。每八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经历着食物供给的不稳定。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获得所需的食物。在充满琳琅满目的食物商店旁,想到仍有一些人正在挨饿,让我深感悲痛。
许多基督徒会利用大斋期或其他禁食时期来与饥饿者共感——去为穷人募款,或提高人们对此议题的意识、提醒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我的一些朋友在大斋期间只吃米饭和豆类,以表示与那些别无选择的人同在。每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饥饿感就像提醒我们的便利贴一样,让我们记得为有需要的人祷告。
当我们在群体中一同选择与贫穷者站在一起,并一起进行禁食,可以让我们超越我们自我中心的视角 (仅仅视禁食为个人灵命的操练)——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在我们圈子之外所有人的经历。先知以赛亚不但没有指责这样的禁食是 “表演性的”,反而赞扬借着这样集体的禁食,我们 “释放被冤枉囚禁的人……与饥饿的人分享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 (以赛亚书58:6-7)。
至于我个人的禁食经验,每次的差异都很大。我永远无法预知圣洁的饥饿感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透明容器,我可以感受到上帝对祂所造世界的爱从四面八方涌出。我得到清晰的头脑和生命的突破,而我的祷告似乎 “大有功效” (雅各书 5:16)。其他时候,当我禁食时,我就只是变得很暴躁、执着于我吃不到的食物,感到头痛,觉得这一切都很愚蠢。
但无论我是否能感受到禁食在灵性上的好处,都不会改变禁食本身的价值。
就像傅士德 (Richard Foster) 在他的经典著作《属灵操练礼赞》所指出的,在操练中,我们为上帝分别出一个专属的空间 (我们的身体) 和专属的时间 (例如,星期三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 欢迎祂进入。尽管我禁食的动机很重要,但我不需要把所有有关成圣的事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后才能去做。
我的禁食过于没有章法,动机不够纯正,有的时候甚至——呃——比我预计的还要短,并且也没多令人印象深刻。每当我将身体以禁食的方式献给上帝时,我献上的是一份乱糟糟的礼物。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拿起一些蜡笔乱涂乱画,然后把画放到父亲手中那样。禁食的操练就好像在说:看!这里面有我太沉迷跟依赖的事、有我的享乐和渴望、我的软弱,以及我仅有的一点点力量。祢还要吗? 而祂确实想要!
透过禁食,上帝的心意是将我们从禁欲主义的残酷及放纵主义的瘫痪中解救出来。禁食挑战了我内心的享乐主义,以及高傲地认为物质世界不如灵性世界重要的二分法。当我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时,上帝做了享乐主义或诺斯底主义都做不到的事:祂既重视我们的身体,也重视我们对身体的自制。祂称我们在身体上的舍己为圣洁的。
禁食既能更新我们对身体在灵性意义上的认识,又能尊荣我们的身体为 “上帝以爱精心塑造的、以各样的丰富所供应的”,是我们与上帝相遇的神圣空间。
上帝并不认为我们的身体是次要或无关紧要的。自从上帝将尘土与祂的神圣气息混合创造亚当的那一刻开始,圣经就呈现人类为整合的、全人一体的自我。耶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降临世界。祂既喂饱饥饿的肚腹,也传讲真道。祂既医治身体上的疾病,也赦免罪恶。弥赛亚视人类的每一部分为同等重要的。
同样地,上帝旨在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禁戒食物让我们的灵魂及身体、pneuma (气息) 与soma (肉身) 能够重新联合。藉由禁食,我们让上帝重新掌管我们的欲望,请求祂赐给我们比我们自己所渴求的更好的事物。我们谦卑地祈求祂的国度在我们的肉身上掌权。
上帝也恩慈地揭示了我们在饮食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所具有的 “群体性”。祂邀请我们在饮食方面 “行公义” (弥迦书6:8)。上帝珍视按照祂形象所造的人类身体。这些身体是祂国度计画的一部分。祂关心我们的食物: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为什么吃、以及和谁一起吃;祂关心我们的肚腹和我们的忧伤——无论是我们面前的餐点还是街上饥饿的人。不仅如此,祂所应许的救赎,终有一天将会改变这一切。
对我这位刚回到美国、在早餐谷物走道上不知所措的人而言,这是个极好的消息——这就是福音。
吉妮·威特洛克 (Jeanne Whitlock) 是住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名自由记者兼诗人,她的写作主要是关于神圣的体现,及其各种不同的引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