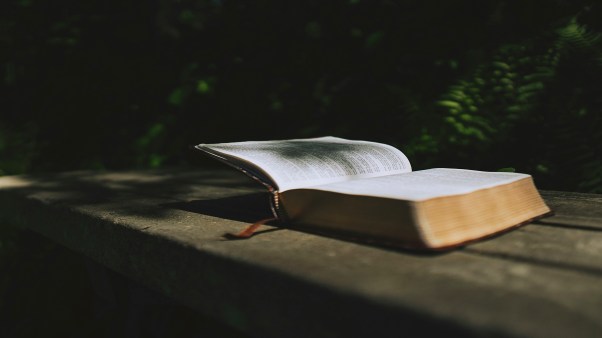伊莉莎白 (Elizabeth Oldfield) 是个失败的无神论者。
她最初是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担任宗教类作家时离开信仰的。然而,现代人 “无宗教生活” 的苍白让她感到不满足。尽管内心充满理智上的怀疑,她依然渴望基督信仰所带来的群体意义及道德愿景。
最终,伊莉莎白接受了一群有知识又善良的基督徒的邀请——他们不畏惧她的提问题,反而透过自身生命样式及爱的品格吸引她回到基督信仰。他们向她展示了一种活出信仰的方式,以真实的生命实践及内在姿态,帮助她活得“更像个真正的人”。
在她的著作《完全活着:在混乱的时代照顾灵魂》(Fully Alive: Tending to the Soul in Turbulent Times) 中,伊莉莎白向读者敞开同样的欢迎之门,尤其是那些抗拒宗教教条,却又渴望意义及光明、向往成为“自由、坚韧、喜乐、勇敢”之人的读者
伊莉莎白现在是The Sacred播客的主持人,住在伦敦近郊一个“有意识地活出信仰”的基督徒群体。 她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勾勒“人类生命真实繁荣昌盛”的愿景:透过 “七宗罪” 的视角。她以机智而博学的方式,重新论证那些古老且顽固的恶行——愤怒、懒惰、贪婪、情欲、骄傲、嫉妒与暴食——至今仍深植于人性之中。她在首章引用基督徒作家施普福特 (Francis Spufford) 的话,指出人类仍拥有一种“把事情彻底搞砸的天然倾向”。
然而,每一种罪也同时蕴含着生命转化/改变的可能。让我们拥抱一个更紧密相连的人际关系──包括使人和睦、群体归属、被爱及喜乐的生命。伊莉莎白以幽默、诚恳且不吝自嘲及悔改的笔触,让这本书充满活泼生动的情感。她谦卑地承认自己也在努力摆脱自我毁灭的习性,努力成为一个 “世界末日时,世界所需要的那种人”。
因为身边有许多 “还没有失败的无神论” 朋友,伊莉莎白谨慎地停留在与那些不认识基督教信仰,或只有初浅认识的人保持对话。她的语调温柔细心,尽力避免弄熄了燃烧中的灯火,或折断对灵性好奇的脆弱芦苇。
她递出的邀请是这样的: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更有爱心、更慷慨的人,冀望以公义及医治来修补这个世界,那么试试基督信仰的道路吧。即使你对其中的某些 (甚至全部) 的真理主张存疑,这条路依然是有益的。放下那 “必须确切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 的沉重负担,采取一些能赋予生命的行动。如果上帝用祂的爱给你意外的惊喜,就让它自然发生吧。
例如,在〈愤怒:从极端化走向使人和睦〉这一章中,伊莉莎白回忆起一次惨烈的经验——她受邀在一场左翼政治集会上代表宗教的观点发言,却遭到粗鲁轻蔑的对待。在试图回应这种难堪处境时,她发现自己无意识地用了作家叶慈 (Jon Yates) 提出的分类概念,粗暴地将人们区分为 “跟我一样的人” 及 “跟我不一样的人”。她解释这种二元对立的动态在人际关系中有多么普遍,无论议题、立场或信仰为何。
当我们屈服于狭隘的 “我们 vs. 他们” 的本能时,就形成了各自的部落,将他人贬低为可鄙视的非人化对象。然而,当伊莉莎白尝试实践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时,她找到了回到对话之中的方法,并能真的祝福那些诅咒她的人。
正如她所观察到的,“那些看起来像敌人的人——甚至可能 ‘视我为敌人’ 的人,实际上都是行走着的、各自充满意义的小小世界——虽遍体鳞伤、却依然美丽,因为人类就是这样,永远有无穷尽的魅力。 ” 接着,伊莉莎白推崇那些无论基督徒、佛教徒、无神论者和其他人都同样认可的、使人和睦的实际行动,例如:爱你的敌人、坚守立场,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打断无止尽的报复循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在整本书中,伊莉莎白展现出作为 “编织社会的人” 的宽厚之心。对她而言,基督教传统并非一块需要守护的故土,而是个好客的暖炉,在这里,各式各样、不同阶层的邻舍都能围坐在一起,共同渴望灵魂及社会的改变。
这本书是与诗人、社会科学家、文化评论家、哲学家及心理学家交织展开的热烈对话。伊莉莎白坐在主位,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贡献想法与意见,最终以她流畅优雅的文字提升整场讨论的深度。在这个充斥着 “意识形态同温层” 的时代,我们都可以从这本试图搭桥的书中得到一些启发。
然而,有一个主题伊莉莎白讨论得不够充足,那就是十字架。在一本关于罪和医治罪的书中,尤其是从基督徒的信仰视角写的书,这无疑是个遗憾的缺口。在书的最后,伊莉莎白解释了她在这方面保持沉默的原因: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这本书中并未多谈论基督的受难……因为我不认为我能让十字架变成一个 “有用” 的东西。这本书是为那些寻找灵命核心力量,以及对基督信仰的具体实践、处世姿态和原则感到好奇的人而写的。这本书并非主要针对那些主动寻求信仰的人……对我而言,十字架是个神圣的地方,只有当你属于后者这一类人时,才该走近它。
所以,在如此动荡的时代,基督的十字架是 “有用的” 吗——能解决我们人类最深层的病痛,使我们真正活出丰盛的生命?
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抛向全球受苦的教会,诸如印度的圣公会达利特人、中国被囚禁的福音派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 (Coptic Christians),以及缅甸的天主教徒。他们或许会告诉我们,十字架是如何成为冲突中的和解典范,是基督无私回应背叛的标志,以及如何作为一顶谦卑的皇冠来对抗这个骄傲的时代。
然而,在这场书中对话的餐桌上,这些来自边缘地带、美丽的基督品格的声音却缺席了。值得肯定的是,伊莉莎白在谈论嫉妒的章节中,曾用一段篇幅探讨基督身体的受难对黑人民权神学家的意义;她也示范了在气候危机面前,基督徒的悔改及哀恸应当如何展现。但我仍然希望能看到更多这类例子。
我确实同意伊莉莎白的看法,十字架是神圣之地。然而,打从一开始,十字架同时也是丑陋的画面,公开地展示给所有人看。它不仅是上帝最伟大的礼物,更完美地呈现人性的真相。土匪和士兵——包括至少一位百夫长,都近距离的目睹这场灾难。他们深陷七宗罪的泥淖之中,却站在这片圣地,近到可以朝上帝之子吐口水。尽管自己如此丑恶,他们之中有些人勇敢地选择了相信耶稣。
无论你是否相信,像这样的事直到今天仍持续发生。
伊莉莎白本可以透过她非凡的沟通天赋,在不贬低读者的智慧,或辜负得之不易的信任之余,将他们带到那个神圣又震撼的场景。
在每一章的末尾,伊莉莎白都会提供读者一两种实践的方式,帮助读者抑制黑暗的冲动,扎根于美德之中。她淡化神学上的差异,超越教派分歧,采取普世对话的方式,寻找与其他信仰传统的共鸣——甚至涉及迷幻药世界的灵性探索。透过邀请我们操练感恩、慷慨之心、寻求 “重新开始” 的对话,以及练习 “科技产品安息日”,她相信这些操练能敞开人们的心思、灵魂及群体来领受上帝的爱。
属灵操练本身有其价值,但终究只是治标之法。对那些愿意像伊莉莎白那样诚实面对自己内心黑暗的读者而言,会需要她仍藏于药柜中的更强烈的解药。毕竟,罪本身是致命的。它能让鲜血流淌,摧毁真实的生命,没有任何 “温和的调整” 能最终抑制它的力量。
这让我想起桃乐丝·戴伊 (Dorothy Day) 在她生命中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位曾是记者,后来创始了天主教劳工运动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的人,在女儿塔玛出生后,渴望抛弃波希米亚式的享乐主义生活,回归儿时的基督信仰。然而,她的挚爱福斯特 (Forster) 却极力反对:
事情最终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该选择上帝,还是选择人?我选择了上帝,于是失去了福斯特。我在1927年12月28日诸圣婴孩殉道庆日 (Feast of The Holy Innocents) 受洗。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我已经厌倦了随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及欲望,随心所欲地行事,这些选择总是让我偏离正道。这个决定的代价,是失去我所爱的男人。
这ㄧ关键的舍己及顺服,带来了她往后无数次较小的牺牲,虽然不完美,她却因此活出了一段光明的爱与怜悯的人生之旅。就如戴伊所经历的,我们终究也须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天抗拒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声音。然而最奇妙的是,这条向着自己而死之路,竟成了我们通往生命的道路。
伊莉莎白说得没错,十字架不是一道可以解开的数学方程式。十字架是一个奥秘,借着恩典真实地呈现出来——当我们弃绝黑暗的行为,披上光明的军装,在一个又一个荣耀得胜的时刻,生命不断地被改变。
亚伦·达米亚尼 (Aaron Damiani) 是芝加哥 Immanuel Anglican Church 的牧师,也是《天堂充满这地:在礼仪、圣礼和教会其他古老的实践中寻找生命 (Earth Filled with Heaven: Finding Life in Liturgy, Sacraments, and other Ancient Practices of the Church)》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