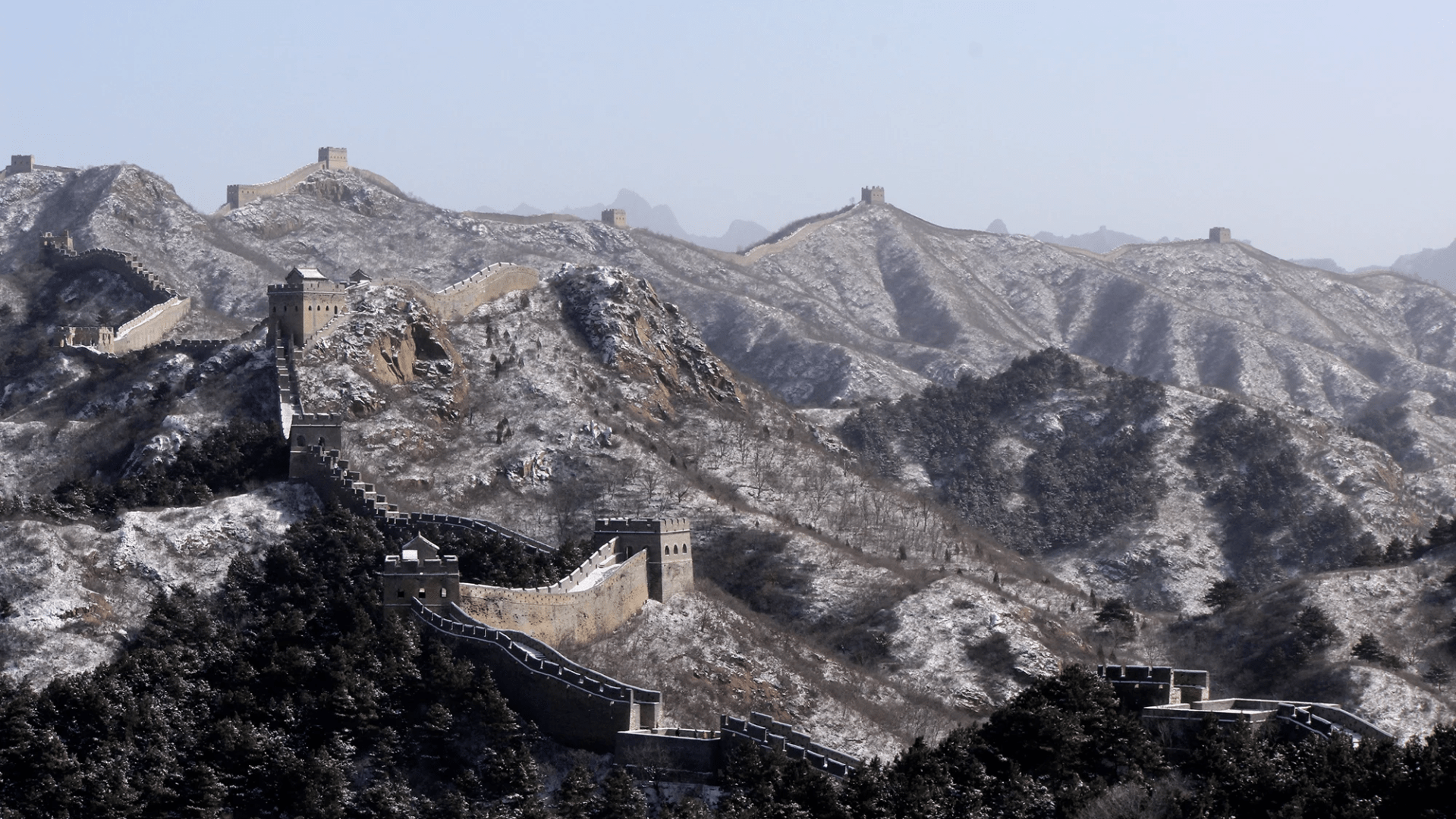大多数的新教牧师认为妇女可以在他们的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但是,在不同宗派之间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
生命之道研究所(Lifeway Research)向美国新教牧师提出问卷,调查在他们的教会里,妇女是否可以担任六种领导角色的位置。在这六种位置中,支持妇女担任主任牧师的仅仅超过半数,但是,支持她们在其他的位置上服事则得到广泛的认可。
有9成左右的牧师认为妇女可以在他们的教会担任儿童主日学牧师(94%),委员会主席(92%),青少年牧师(89%),以及成人查经教师(85%)。
支持女性担任执事(64%)及主任牧师(55%)的人数更少一些,但只有1%的牧师认为妇女不可以担任任何有领导地位的位置。还有不到1%的回答认为不确定。
“不知道背景的人可能会认为,对于女性在教会中可以在什么位置服事的各种不同意见只是出于一些不近情理或过时的观点。但这些不是意见的问题,而是解释圣经的角度问题,”生命之道研究所执行董事麦康奈尔(Scott McConnell)说。“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不同教派的圣经学者对圣经的含义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宗派之间的差异
由于对圣经解释在细节上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新教教派对担任某些领导职务的妇女有不同程度的开放程度。一般来说,主流教会的牧师说,与福音派教会相比,他们的教会对女性可以担任的角色的限制较少。
福音派和主流(mainline)教会的绝大多数牧师都表示,女性可以担任儿童牧师(94%和97%),委员会领导人(93%和95%),青少年牧师(89%和95%),以及男女混成的成人圣经学习教师(84%和95%)。
在执事和主任牧师的角色上出现了分歧。八成的主流教会牧师(79%)表示,执事的角色应该对女性开放,而56%的福音派牧师同意这一观点。在主流教会牧师中,76%的人说女性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只有不到一半的福音派牧师(44%)也这么说。
“与其他领导角色相比,一些牧师之所以把女性担任牧师与担任执事甚至教导男性区别开来,是在于他们如何解释圣经,”麦康奈尔说。“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他向教会发出关于这些具体角色的指示。但新教教会对他的意图有不同的看法。”
所有宗派团体的大多数牧师都说,妇女可以成为儿童的牧师,青少年的牧师,委员会领导人,或者在他们的教会中男女混同的成人圣经学习教师。
具体来说,卫理公会和五旬节派牧师比复原主义运动、信义会和浸信会牧师更有可能说妇女可以成为儿童或青少年的牧师。卫理公会教徒最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成为委员会领导人(98%),最有可能允许女性在教会中成为男女混同的成人圣经学习教师(100%)。信义会(77%),浸信会(74%)和复原主义运动(62%)牧师最不可能说他们的教会对女性担任男女混同圣经学习教师持开放态度。
大多数卫理公会(88%)、五旬节派(83%)、长老会/改革宗(81%)、无宗派独立教会(79%)和信义会(60%)牧师表示他们的教会允许女性担任执事。大约一半的复原主义运动(49%)牧师同意。浸信会(29%)最不可支持女性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执事。
超过3/4的卫理公会(94%)、五旬节派(78%)和长老会/改革宗(77%)的牧师说,女性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信义会(47%)和非宗派独立教会(43%)的教会更加分裂,而更少的复原主义运动(25%)和浸信会(14%)牧师表示,他们的会众对女性担任主任牧师开放。
“虽然新教有一些历史分支中的个别教派太小,无法在这项研究中单独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类别中的教派在这个主题上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就像在不同的信义会和长老会教派中经常看到的那样,”麦康奈尔说。
其他人口统计学的差异
宗派并不是揭示女性在教会中角色差异的唯一因素。
年长的牧师和小教会的牧师更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担任主任牧师。年长的牧师——55至64岁(60%)和65岁及以上的牧师(59%)——比18至44岁的牧师(49%)更有可能说他们的教会允许女性担任主任牧师。出席人数少于50人的教会的牧师(66%)和50至99人的牧师(59%)比100至249人的教会的牧师(46%)和250人或以上的牧师(41%)更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成为会众中的主任牧师。
非裔美国牧师最有可能说,女性可以在他们的教会中担任青少年的牧师(97%),并且比白人牧师更有可能说女性可以成为男女同校的圣经学习老师(95%对84%)。
美国东北部教会的牧师对女性在某些方面担任领袖更加开放。他们是最有可能说女性可以作为执事(77%)或男女同校的圣经学习老师(89%)在他们的会众中做领袖的人。
“虽然使徒保罗提到了几个特定教会角色的差异,但男女在教会中地位的任何差异都到此为止,”麦康奈尔说。“当讨论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时,他教导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
翻译:贺宗宁(T. N. 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