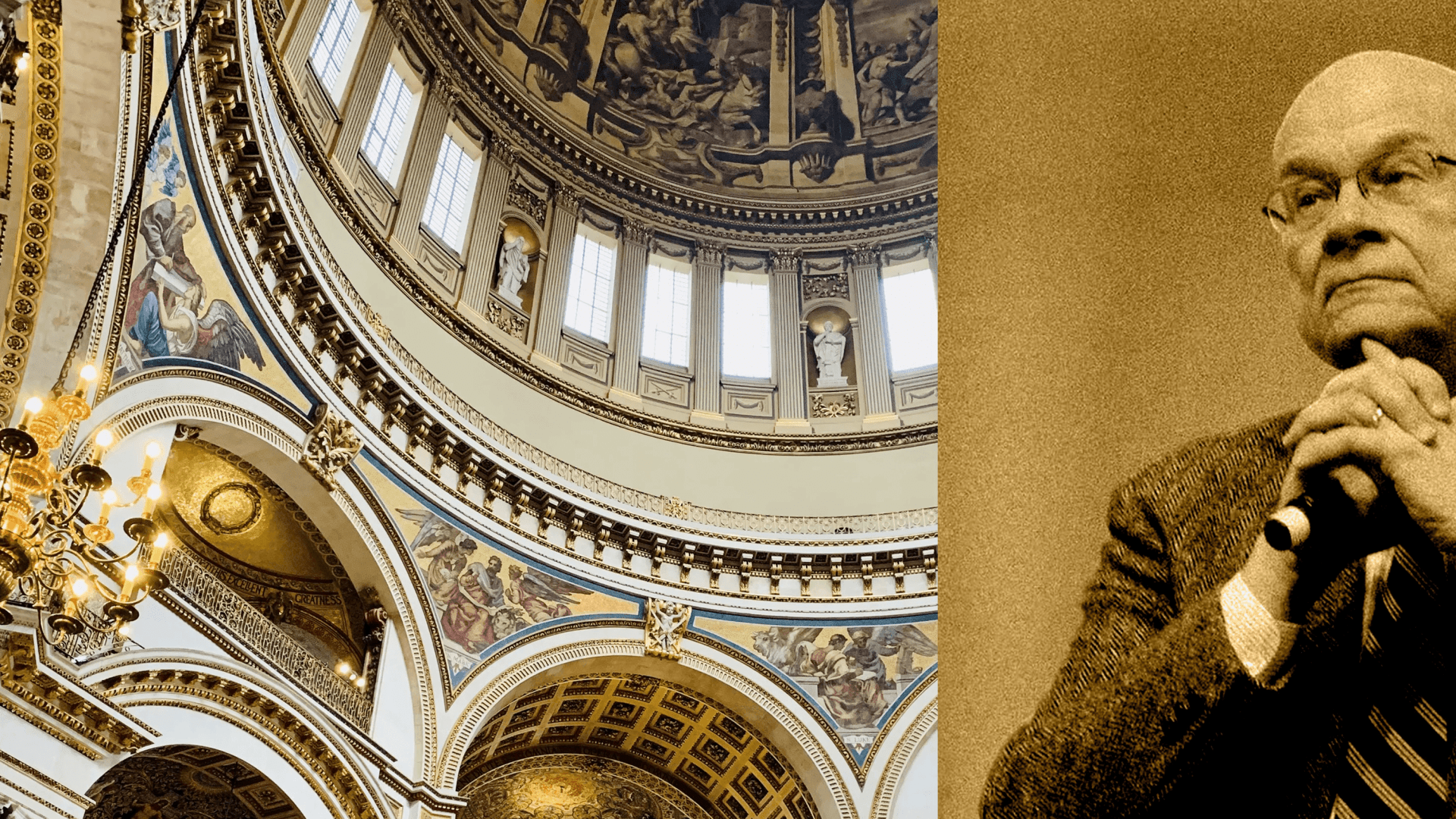据估计,今日有2900万名妇女的生活状态类似“现代奴隶”,包括某种形式的性贩卖(sex-trafficking)和强迫婚姻(forced marriage)。为了了解为什么在亚洲有这么多女孩和女人遭受性贩卖的伤害,希薇亚·居·傅利曼(Sylvia Yu Friedman)希望更多人能回顾其历史渊源。(编注:“性贩卖”非指女性自主的卖淫行为,而是出于他者、强权或经非法买卖下强迫女性卖淫)
“专家估计,日本帝国军队从他们占领的国家带走了多达40万名女孩和女人,送到位于中国的1000多个强暴站点和整个亚太地区士兵驻扎的数百个军事妓院,”她说。 “联合国专家称这是20世纪对女孩和女人最大的人权侵犯。然而,日本政府始终不愿承担战时性奴役计划的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也未发出真正诚恳的道歉,满足幸存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要求。”
虽然政府并未承担完全的责任,但分别有日本基督徒亲自向在中国的日本战时性奴隶的年长幸存者道歉。
希薇亚说:“他们对这些幸存者和其他中国人及韩国人的真诚道歉,为战争的创伤所产生的世代痛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愈合。”
身为一名作家、电影制片人和慈善家,希薇亚采访了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强制从事性奴役和今日在性贩卖集团控制下幸存的亚洲女性。
她说:“我意识到,亚洲仍然存在着性贩卖的回圈,由日本军队开始的性奴隶事业未曾消失或结束,因(亚洲各国的)性别歧视的普遍事实和缺乏对战时性奴隶这个历史事实的强烈谴责。”
希薇亚对终结性贩卖的热情使她二十年来一直在调查其背后黑暗的地下社会结构。透过她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工作,她成功地把资金引至一些早期的亚洲反贩运计划里。
希薇亚也透过“852自由运动(852 Freedom Campaign)”组织研讨会,教育更多人了解性贩卖的问题。身为对抗性贩卖的先驱者,她以香港为基地揭露不同形式的性贩卖罪行,并因她制作的关于中国、香港和泰国人口贩运的三部曲系列纪录片而获奖。希薇亚也是《通往正义的漫长道路:来自亚洲前线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目前正与一家位于新加坡的电影公司合作,制作一部以该书为基础的电视剧。
希薇亚近期与《今日基督教》全球书籍编辑Geethanjali Tupps谈及她对亚洲人口贩卖地下社会的调查,以及她是如何因着这次旅程接受了自己的韩国身份、目睹亚洲职业女性改变当前性贩卖情况的潜力,以及见到祷告带来的影响力。
你最初是如何对打击性贩卖燃起热情的?
我对人权的委身起源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在1980年代,我是加拿大一所全是白人的学校里唯一一个韩国学生,我遭受到种族主义的强烈羞辱。除了路上的陌生人会叫我中国佬(chink),同学们也会说“中国佬你(chink you)”而不是“谢谢你(thank you)。”我的朋友们会对我的外表发表些不得体的评语,或问我家的泡菜罐里是否装着死掉的动物。
所有一切都让我对不公正的现像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我十几岁那年,我母亲转述了一份韩国报纸上关于金学顺(Kim Hak-soon)的故事,她是二战期间为日本军队强迫卖淫的幸存者。金学顺向国际媒体作证她的“慰安妇”人生经历:她在青少年时期被迫为日本军队卖淫。金学顺愿意公开分享她的故事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否认曾实施战时性奴隶制度,并且称这些女性为“自愿性的娼妓”。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在学校课本里没有学到这段历史。我无法忘怀这个事实:如果我在那个时期出生在她的家庭,她所经历的事可能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后来对战时性奴隶制度有哪些方面的了解?
在乌克兰和奈及利亚,战争中的性暴力透过像博科圣地(Boko Haram)这样的恐怖组织而存在。全球有630万名女孩和女人受着性贩卖的折磨,这个回圈仍持续不断。
我相信性贩卖的回圈,是由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性奴隶制度延伸下来的。战后,一些韩国和中国的受害幸存者被留在如泰国等国家,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在军事基地附近卖身。如果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二战后对战时性奴隶和“慰安妇”政策的丑行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并宣布人类应“永不再犯”这样的罪行,今天是否会不一样?强硬的立场也许能使国际间达成协议,协力阻止贩卖女性。
你的人生在调查人口贩卖的地下社会长达20年后,有什么样的转变?
2013年,当我在香港为性贩卖纪录片做研究时,我首次和一位宣教士进入红灯区,寻找受害者进行访问。我非常害怕,一度想要抓住宣教士的手——如果他能接受我这位成年的职业女性有这种行为的话!
当我们在外面时,我们遇到一位年轻且充满创伤的母亲,她被迫整夜寻找“恩客”。虽然她并没有身体上的束缚,但贩卖她的人对她有另一种更邪恶的掌控:他们知道她的女儿和祖母一起住在非洲,并威胁要伤害她女儿。我们尽力想出方法帮助这个受害者,甚至带她去过教会,但她的电话号码被切断,她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经历过许多可怕的情况。我在采访性贩卖受害者时,曾在妓院里遭到一大伙暴徒的威胁。我也曾需要在武装士兵的保护下在边境地区工作。
这些经历让我坚信祷告的力量。我见到我的母亲和朋友为我热切的祷告,当我从这些臭名昭著的红灯区一次次的危险遭遇中毫发未伤地离开时,他们的祷告有了真实具体的影响。
我在缅甸边境附近最恶名昭著的红灯区拍摄期间,有一次濒临死亡的经历。我们被暴徒和妈妈桑包围,他们指责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们妓院的影片,但我未曾这样做过。我的人生跑马灯在眼前一闪而过。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警察来了!”他们就像蟑螂一样四散逃跑了。但这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我相信那次是一个活生生的奇迹;一位我的朋友那时正在为我祷告。
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我的信仰推动着我透过写作、慈善活动和电影去倡导、为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们发声,提高人们对现代奴隶这个可憎事实的认识。
我的书正是我的见证——见证关于神如何在我自己、那些前线工作者、现代奴隶制下的幸存者,甚至那些我在路程中遇到的加害者、人口贩子的生命里工作及改变我们。我旅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在祷告和我的导师、牧师及朋友的支持下前行。
和你交流过的幸存者是如何影响你对性贩卖的理解的?
我遇到了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幸存者金顺德(Kim Soon-duk),那时她已经83岁。
金顺德是个温柔的人,但她的经历让她在55年后依然受到很深的创伤。尽管如此,她对日本人没有怀有任何怨恨,只希望我将她的故事告诉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她渴望在去世前能收到日本政府真诚的道歉。
我接着见到和采访了其他几十位不同国家战时性奴隶的幸存者,包括中国。见到这些抵抗自身亚洲文化保守价值观、发声抗议数十年之久的年长幸存者,是个神圣的经验。
这些妇女是他们国家第一批#MeToo社运人士,他们长期站在反对性贩卖和战争下的性暴力罪行的最前线。他们值得得到他们迫切追求的目标和尊严。但这些幸存者年纪渐长,而时间不多了。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援。
你从幸存者那里听到哪些关于基督徒的工作?
我曾与被贩卖进入强迫婚姻且被迫从事网上卖淫生意的北韩妇女谈话。她们告诉我,有些南韩宣教士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她们沿着一条地下铁路前往首尔,并获得公民资格和政府的支持。在其中一个采访中,我听说一位年迈的南韩牧师几年前在带领一群北韩妇女穿越一条暴涨的河流时去世。
通过希望之门事工(Door of Hope),我认识了一些勇敢的中国年轻女基督徒,她们无畏地用上帝的爱去接触被贩卖至红灯区的妇女。这些妇女的信仰帮助她们克服自己原本对卖淫妇女的成见,以及最初不支持她们的家庭教会的成见。今天,她们不断拯救着被卖的妇女,并为幸存者和一些人贩子提供工作和康复的机会。
曾与你有所交流的男性是如何帮助完成你的书的?
我被一位以前曾是人口贩子,如今成为东南亚宣教士的人的见证深深感动,他对现代奴隶买卖这个地下世界的专业知识为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与年长的前日本军人会面帮助我理解军队性奴隶犯罪者的心理。我还有幸见到几位勇敢的日本基督徒,他们认为向中国人和韩国人表达个人的歉意是他们的使命,且他们的行动也带来了深刻的治愈。
日本军队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造成的跨世代战争创伤,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且持续为中国、香港、韩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痛苦、创伤和种族仇恨。
长期从事性贩卖的报导对你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
我有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持网络——我的家人、丈夫、朋友都支持我,我很幸运,我还没有遇过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也并非全职在前线工作(那里的风险更高的),只在采访和记录性贩卖案件时才冲进现场。
然而,我在中国的红灯区有过濒临死亡的经历,也有过创伤。在早期采访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年长幸存者时,我也有过二次创伤,主要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没有建立足够的心理界限,我想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写出共鸣。
报导性贩卖对你的韩国身份认同有什么影响?
这段旅程的一个副作用是,我已完全接受了我的韩国血统,这是我身份的一个层面。由于我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种族偏见,我曾拒绝接受自己的韩国身份。然而,在中国生活帮助我接受了我的文化传统。
因为我不会说流利的中文,陌生人会问我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或者他们认为我是海外华人。我经常得面对我的文化遗产,比我住在加拿大时还要多。当我提到我是韩国人时,陌生人几乎都会说他们喜欢韩剧和音乐,并说韩国人有多酷。这总是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是在一个亚洲文化不被视为“很酷”的时代长大的。
与韩国性贩卖幸存者的会面让我看到,无论我多努力地拒绝我的韩国文化遗产,我的基因里仍是韩国人。当我了解到日本殖民主义和慰安妇的情况时,我有一种直观的反应,我把它归结为一个世代的仇恨/痛苦——我会说这种情况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日本集中营幸存者的情况相似。
是什么给了你盼望?
100多年前,像我这样的亚洲女性会被迫裹小脚、被视为别人的财产、结婚前没有名字,也不被允许受教育。
自那时起至今天,我们已走过漫长的道路,如今有影响力的亚洲女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还多。但在改善亚洲女孩和女人的权利和尊严方面,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听说过在北韩被贩卖为新娘的女性,夫家为了防止她们逃跑而要她们整天在田里工作,只给她们穿薄薄的拖鞋;我也曾见过一个像狗一样被锁在自己家里的女性。
去年,在中国苏州,一位被贩卖的妇女——身为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锁在房子里的照片引发了全国的讨论。从我在中国听到的消息来看,那里的“反人口贩卖运动”正在萌芽发展,我相信这是因为职业女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她们对妇女遭受到的可怕剥削感到愤怒。
我的朋友艾真(Ai Jin)透过希望之门事工接触性交易产业内的女性已有数个月,但当她发现自己14岁的表妹也被拐卖成了妓女时,她悲恸万分,一度想放弃。
在我的书中,我写道:“艾真帮助强化了这个观点:普通人也能做出非凡的英勇行为。她承认自己很软弱,经常想要放弃。但是,她对上帝的坚定信仰让她继续闯荡在性贩卖和卖淫的世界,而她的信念对我也是个挑战。”
透过认识像她这样的人,我开始梦想着,如果有一亿个中国基督徒加入反对现代奴隶产业的战场,他们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翻译: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