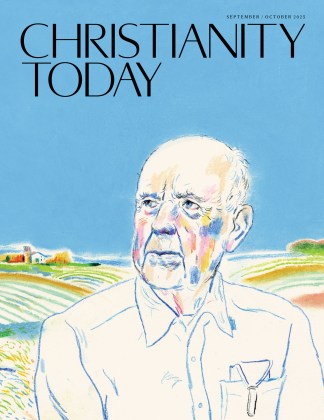从许多方面来看,我的人生见证没什么特别之处。我在一个稳定的家庭中成长,父亲从事全职事奉,母亲则在家中照顾我,因我是一位有学习障碍的小孩。六岁那年,我决志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我的主和救主。我常常问父母许多关于信仰的问题,直到我亲自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信主之后,我就是个典型的 “教会孩子”。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不跳舞——虽然这主要是因为我非常害羞,而且毫无节奏感。我青少年时期唯一的叛逆行为,不过是偶尔说几句脏话,以及一段过于认真的青少年恋情。
十年级时,上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一向是个倾向讨好别人的人,也很害怕孤单。为了避免感到孤立,我总是待在人群之中。那ㄧ年开学的第一天,我到学校才发现自己在班上一个朋友都没有,连午餐时也是形单影只。这种光景现在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对青少年时期的我而言,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天晚上,父母陪我度过那场青春期的情绪崩溃,并鼓励我带圣经去学校。
这个建议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我开始带着圣经上学时,我也开始经常阅读它。原本我依赖别人来填补友情的空缺,现在耶稣成了我的挚友。随着我和上帝的关系日益加深,在那一年内,我清楚感受到上帝呼召我进入全职事工。
时间快转约十年后,我来到奥克拉荷马州邓肯市 (Duncan, Oklahoma) 一间浸信会教会担任牧师,那是一段极具挑战的时期。这间教会多年来持续在衰退,在我到职前,他们已曾试图开除三位牧师中的两位,而教会里确实有一部分人对我没有好感。
身为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有人不喜欢我” 这个想法总让我很困扰。虽然他们聘请我来牧养年轻人,但实际上,我的工作似乎是维持现状、迎合教会中年长的成员。
在这间教会第一次重大冲突的爆发,是因为一位女士对我一岁和两岁的孩子经常在教会出现感到不满。她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这间教会快要永远关门了,这完全是因为你的孩子们。” 可是,当时我的孩子既未失礼也没有捣乱,他们只是单纯地 “在那里”。
几个月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有两个男孩之所以勉强来青少年团契,是因为教会能提供巴士接送。他们戴着鸭舌帽,坐在教会最后一排椅子上。一位执事告诉我,那两个男孩要嘛脱下帽子,要嘛就得被赶出教会。我告诉他,这两个孩子正是我们蒙召要去和他们分享上帝的爱的人,有没有戴帽子根本不重要。这番话,让我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第三次冲突则发生在我女儿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当时,我和妻子珍妮佛因在教会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车贷,我们一直共用同一台二手车。女儿们开始上学后,我们意识到我需要另一种代步工具。于是,我们买了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东西:一台50 美元的大卖场脚踏车。我开始每天骑脚踏车往返教会。但我不知道的是,许多教会成员有时会特地开车经过教会,查看牧师是否有来上班。当他们没看到牧师车位上有车时,就以为我没去工作。
在某晚的教务会议中,一切的矛盾终于完全爆发。对一位牧师而言,浸信会的敎务会议就像85个老板同时出现,抱怨你做得不够好。但那场会议与往常截然不同。平常我们教会的主日敬拜约有85人出席,那晚却来了至少150人。在我发放年度预算资料,接着开放大家讨论时,一个想将我赶走的计画渐渐浮现。虽然反对我的那一派没有达到解聘牧师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但他们似乎握有超过一半的票数,足以将我的薪资方案从教会预算中删除。那天,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都在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对着我大声咆哮:嫌弃诗歌的选择、责备我用iPad讲道、抱怨我允许那些 “叛逆的小鬼” 戴着 “叛逆的帽子” 进到教会——当然,还有抱怨我的孩子们。
我泪流满面,心碎至极。最后投票结果出炉,反对派只以两票之差失败。但几周后,一半的会众离开了教会,教会就此分裂。
苦毒开始在我心中萌芽。
同年稍晚,我们怀着破碎、受伤与疲惫的心离开了奥克拉荷马州,搬到休士顿,我们相信新的开始能医治我们心中的苦毒。
在下一间教会服事时,我们又面临到一连串崭新的挑战。我仍试图透过 “讨好他人” 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还是没有用——毕竟,只要忽略伤痛,它就会自己消失,对吧?
时间快转到我目前牧会的地方,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间教会。人们常说 “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创伤”,但老实说,若从未正视伤口,时间并无多大助益,反而是伤口会化脓扩散。我还记得刚到教会的前几周,初次与弟兄姊妹见面时,我总忍不住思忖:这些人之中,哪些人未来会伤害我们? 当我们结识新朋友时,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以往教会成员的影子——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这些年来,能触发我悲伤的事越来越多。有些日子,我从教务会议回到家,仍能感受到多年前那深沉的痛再次涌上心头。几周前,有人对珍妮弗说了一句贬损的话,让她忍不住落泪——那些多年累积的教会伤痛再度涌上心头。我也说不清有多少次发誓要永远退出Facebook,因为人们常在上面公开评论我的事工与生活。
两年前,珍妮佛和我开始在名为 “安全区”(The Landing) 的学生事工中服事。那里有时会邀请我上台报告,而这意味着我要分享自己的挣扎。起初我只说一些表面的事,但随着时间过去,那不断提醒我们要面对自己的习惯、困境与伤痛的信息,驱使我正视那片深不见底、我从未处理过的痛楚之海。我终于明白,自己之所以沉溺于食物、健身、讨好他人、苦毒与愤怒,其实都根源于那些在多年事奉生涯中累积、深埋心底的伤口。
大约一年前,珍妮佛和我前往丹佛市参加一场教会研讨会。我提议不如顺道带孩子一起去度假,并绕道回奥克拉荷马探访我们曾牧养的教会——在那里的经历从未在我心里真正划下句点,我们从未好好处理那份伤痛。那趟旅行八个月后,我接到一通来自那间教会的电话。原来,上帝也在他们当前牧师心中放下同样的感动。他们邀请我回去担任培灵会的讲员。
那一刻,无数情绪涌上心头。我答应了。
当我们抵达邓肯市参加培灵会时,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但上帝早已预备好这一切,祂知道我需要医治。我们见到了当年的朋友,他们仍然爱我们。后来我与现任牧师交谈并分享我们当年的经历,他诚恳地向我们道歉。
在复兴聚会的第三个晚上,我们当年的 “麻烦制造者” 之ㄧ走进了教会。如果说我在开车进入邓肯市时心跳加速,那么当那个人出现的那一刻,我的心几乎要炸开。离开奥克拉荷马的这些年里,我无数次想像过这一刻——在我的想像中,我终于能当面痛斥他一番。
然而,上帝柔软了我的心。那个人虽没有为他当年加诸于我家人的伤害道歉,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上帝已赐给我平安。那一刻的饶恕,不再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而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份礼物。
牧师并非完美无缺的人。笑容的背后,我们多半都带着伤痛。身为牧师,我常常不愿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老实说,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也在挣扎。我害怕人们会利用我的软弱来攻击我。
我的医治之路至今仍未结束。光是这个礼拜,我就曾因听到一些直接而尖锐的话语而情绪低落。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忧虑与心痛就像恶魔般袭击我,使我辗转难眠。我仍然有一些苦毒尚未完全交托给上帝。然而,在这持续的挣扎中,我仍怀着感恩之心信靠耶稣基督。我能看见祂正在引领我,帮助我学习将一切重担和忧虑交托给祂。我也看见上帝正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带来医治。
Wes Faulk现任路易斯安那州维达利亚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Vidalia) 主任牧师。本文原刊于他的个人网站wesfaul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