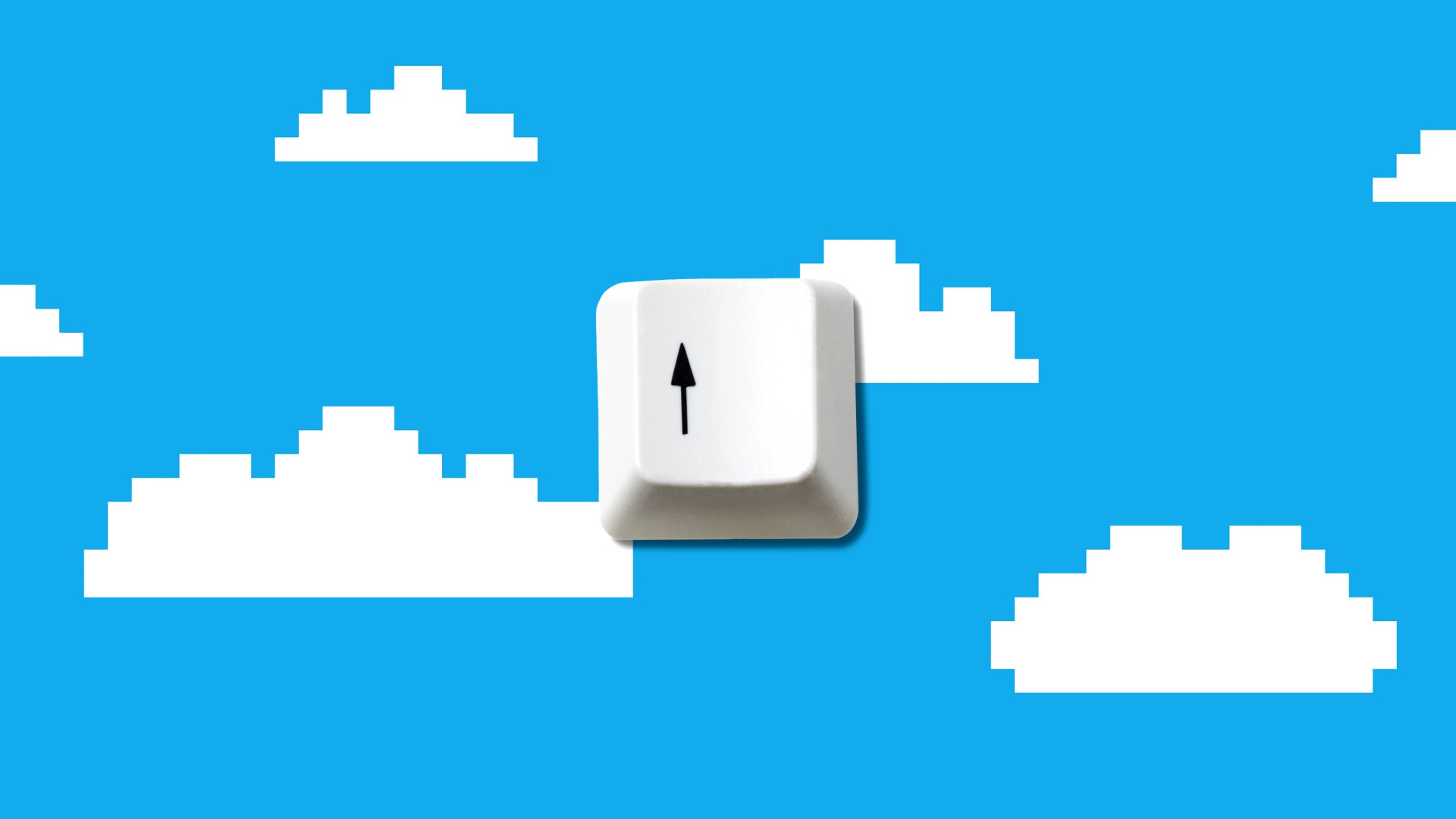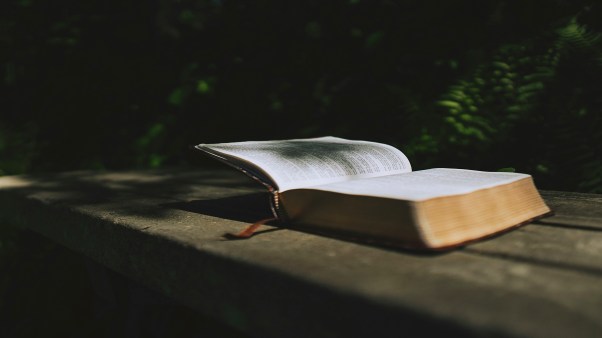随着宗教信仰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渐下降,Z世代在探索身份认同、归属感和人生意义时,能求助的资源和人也越来越少。因此,我们转向网路寻求答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是Z世代的一员,对这种倾向很熟悉:与其麻烦店员,我更倾向用超市的app找我需要的商品。表面上看来,转向网路寻求答案似乎有些反社会,但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高度自主/独立的文化和Z世代广泛使用网路的特性。
这种趋势自然也延伸到了教会。随着参加教会的Z世代人数减少,年轻人更倾向在虚拟空间而非实体空间中寻找人生大哉问的答案。
然而,我相信Z世代中那些无特定宗教信仰的人,比数据所呈现的对信仰更感到好奇。宗教归属感通常很容易衡量,但灵性好奇心及开放的态度则难以量化。在网路上,我们能看到年轻一代提出的种种问题,以及有哪些人前来回应这些问题。
一个不错的例子是《Girlscamp》播客,这是一个为前摩门教徒提供信仰过渡期的支持的播客。主持人海莉·罗尔(Hayley Rawle)在节目中访问前摩门教徒、分享听众匿名投稿的故事,并探讨摩门教信仰的不同方面。
在《Girlscamp》中,海莉鼓励听众离开对会众高度要求的宗教后,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她为听众提供一种“真理是相对的”的世俗哲学,以此替代高要求的宗教僵化的界限。我约在一年前发现海莉的播客,尽管她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摩门教,但她也公开批评基督教会和西方基督教。她的播客是Z世代如何在不参与实体社群的情况下接触灵性议题的例子之一。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基督徒被人们告知“Z世代的生活几乎没有宗教的影子”。似乎有一种观念认为,人类曾是非常有宗教性的,如今再也不是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表面上看来,Z世代似乎越来越不宗教化,因为在宗教归属调查中,许多人选择了“无特定宗教”。有高达一半的Z世代认同自己没有特定宗教信仰,因此人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Z世代对灵性/灵命不感兴趣。然而,我们对灵性的追寻与前几代人类一样,只是换了别种表现形式而已。
伊利诺伊东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莱恩·伯奇(Ryan Burge)指出,“无神论/不可知论”的认同率在每一代人之间都逐渐增加,直到千禧世代与Z世代的过渡期间,这种趋势转变为“无特定宗教(nothing in particular)”且这类人的比例持续增长。
泰尔博神学院(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哲学教授提摩太·皮克万斯(Timothy Pickavance)认为,“无特定宗教”类别的增长表明Z世代对灵性的开放态度,而非一种愤世忌俗的无神论立场。
“这些数据显示Z世代对灵性议题的敏感性,以及他们对深层次的灵性生活的渴望,”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
Z世代宗教参与的方式可用“信仰拆解(faith unbundled)”一词来概括,这一术语由《春潮研究所》(Springtide Research Institute)提出,描述人们如何从各种宗教和非宗教来源中组合信仰的要素,如信念、身份、实践和群体,而不是从单一的宗教体系中获取这些要素。播客主持人和网红——如前面提到的海莉,在某些方面成为数位牧师或灵性导师的角色——成为提供宗教要素的非宗教来源之一。她的受众在这些平台上接触到一种世俗的“福音”,其中的“好消息”便是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宗教信仰,保留自己认同的教义,摒弃对自己设下限制或自己不认同的教义。
无特定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每周收听播客,像宗教人士可能每周聆听主日礼拜讯息那样,学习如何实践自己的灵性。在《Girlscamp》其中一集里,一位嘉宾谈到用周日晚餐时间让家人轮流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来取代祷告。与其分享圣经中的故事,这位来宾选择教导他的孩子一个关于爱或包容的世俗课题,作为一种替代的灵性实践。
基督徒和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宗教参与很不真实。但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非物质世界的这种开放态度,却也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及交流提供沃土。
虽然Z世代正在放弃传统的宗教机构,但他们并没有放弃灵性/灵命生活。在1990年代,人们开始从使用“宗教的(religious)”一词转向使用“灵性的(spiritual)”一词来描述个人的道德和灵性框架。如今,这个词汇又演变为“建构意义(meaning making)”。
“上帝”和“群体”曾是人们宗教生活的中心,但对Z世代而言,这些已不再是有意识地过着灵性生活的先决条件。正如皮克万斯(Timothy Pickavance)形容的:“人们对灵性的渴望和明确的追求仍然存在,只是没有融入到某个特定的宗教传统中。”
康沃斯大学(Converse University)牧师德爱丽莎(Eliza DeBevoise)经常为学生们解答人生的重大问题。她认为Z世代是极其追求灵性的。 “无论Z世代是否信仰宗教,他们在灵性塑造方面都非常非常地努力,”爱丽莎说。 “坦白说,我之前未曾在更虔诚的老一辈人之中见过像Z世代那样的努力。”
爱丽莎指出,即使学生有强壮的个人信仰,他们也很难认同单一种宗教。即使是虔诚的学生也会担心自己被人认为是思想狭隘的人。
像之前的每一代人一样,Z世代的心中也带着对永恒的渴望。但这种对超越自身的事物的渴望,无法透过个人自己的灵性探索完全满足。我们需要教会。
正如卢云神父(Henri Nouwen)在他的著作《一棵树栽在溪水旁》(Spiritual Formation)中所写:
“灵命塑造并非一种私人虔诚的练习,而是一种共同的灵性生活。我们确实会有个人与上帝相遇的经历,但我们是作为上帝的子民共同被祂塑造的。”
人类所感受到的宗教冲动,在信仰群体的环境中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种冲动正是教会可以回应的。
像海莉这样的线上导师能在不认识跟随者的情况下指导他们的灵性旅程。这一点让那些有兴趣探索宗教解构的人的风险较低。虽然我们确实能在网路上进行有意义的灵性探索,但我们并非注定要在孤立的处境下回答这些问题。
年轻的基督徒同样可能有仅仅透过网路来参与基督信仰的诱惑。但播客、网红或基督教书籍应是促进人们面对面时“成为一个群体”的催化剂,而非取而代之的选项。
虽然教会群体并不完美,但透过每周、每月、每年不间断地聚集所成为的道成肉身的群体,仍是基督徒灵性生活的核心。仅仅在个人层面实践的灵性生活是不完整的。
有研究表示,青少年每天平均花约9小时在频幕上。尽管成为网路社群的一份子可能是Z世代的常态,但这不应该是教会投入精力的主要方向。即便有许多优质的基督教线上资源可以对抗世俗主义或解构性的内容,年轻人需要的远不只是资讯,而是群体——而群体始于具体实际的关系。
我能为真诚的友谊如何成为人类信仰的催化剂做见证,因为那正是我成长的故事。正是那些关心我的成年人在我生命里的投资,让我拥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探索关于上帝的问题。身为Z世代的我知道,无论如何,我在这里都会被爱和被接纳。
如今,作为《Young Life》事工机构的领袖,我和其他人正在学习如何在教会内外建立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教会之外的替代空间,让年轻的女性可以遇见耶稣,例如在午餐时间与她们一起用餐、带她们去喝咖啡或观看她们的体育比赛。从这些互动开始,我们还举办查经班,并有机会与她们进行灵性的对话,邀请她们加入信仰群体。
与其整日批评年轻人花在网路上的时间,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一个充满爱、具体存在、不完美的群体。
正如玛丽·德穆斯(Mary DeMuth)2011年在本刊所写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式的文化中,这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孤立。我们这些在网路上创造人设、精心隐藏自己的人,可能会觉得融入地方教会令人害怕。然而,上帝呼召我们成为教会,无论教会有多少缺陷。祂呼召我们与其他耶稣的门徒立约同行,将我们的生活与那些我们平时可能不会接触的人混合在一起。在这种融合的群体中,我们学会彼此相爱的艺术,而这样的爱向圈外人展示耶稣是什么样的神。
对那些因各种原因避免参与任何社群的人来说,加入一个面对面的信仰群体确实存在风险。你不能保持匿名性,也无法在感到不舒服的时刻马上登出帐号。但你同时也获得一个被了解及被爱的机会——这是线上社群永远无法提供的。
珍娜·敏德尔(Jenna Mindel)是本刊NextGen Accelerator Fellow的研究员。她近期毕业于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主修新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