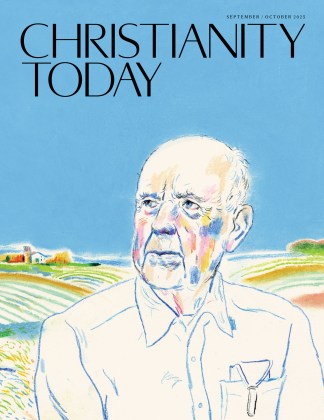本文原发表于2022 年三月
上周,美国最高法院提名人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因拒绝为“女人(woman)”一词下定义,引起轩然大波。在回答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的问题时,杰克逊回避了这个问题,她说:“我不是生物学家。”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追问杰克逊,“性别歧视诉讼案”所保护的对象包含哪些人?杰克逊再次推辞,称这类案件目前正在低阶法院进行。
保守派很快就对杰克逊进行抨击,认为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进步派在胡言乱语的明证。毕竟,任何人都应该能够定义什么是女人。然而,唯一的问题是,过去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努力定义何谓女人。
无论是将女人视为“残缺版本的男人”的古希腊人,或是不相信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教父们,历史的记录都显示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该如何看待女人。即使在我们国家的过去,女人也一直在努力争取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些造物主所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基督教护教家及学者榭尔丝(Dorothy Sayers)在她于1947年发表的文章《不那么人类的人类》(The Human-Not-Quite-Human )里反思我们对女人的定义的不足之处:
研究任何现象的首要任务是观察其最明显的特征。 ……大多数研究如何“定义女人”这个难题的学生都在这第一个关卡失败,而教会在这议题上比多数人更可悲,也更没有借口。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论述,这类讨论从一开始就失去其意义,因为当人们讨论男人时,总是讨论其身为人类(Homo)及雄性(Vir),但讨论女人时,只会讨论其身为雌性(Femina)。
榭尔丝认为,“女人(woman)”一词的准确定义必须同时包括其女生属性和人类(human)属性,“人”是名词,“雌性(female)”是形容词。毕竟,很多东西都有雌性——猫、鸟,甚至一些树——但一个女人的权利和责任源自于其共有的人性(humanity),而非她所属的性别(sex)。雌猫没有公民权利。雌树没有公民权利。雌性人类却有。
换句话说,除非我们对女人有一个可行的定义,即“女人本身就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而不仅仅是“与男人相反的那个”,我们同样也会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失败。
诚然,榭尔丝当时所强调的困境似乎与我们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不同。毕竟,参议员布莱克本提出的问题是,“跨性别女运动员能否参与女子运动竞赛?”
从男性变性成女性的人能否合法地宣称自己是名“女人(woman)”?法律在处理性别歧视案件(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时,是否也包含他们?与当年主张女性的“人格性(personhood)”的榭尔丝不同,我们挣扎于定义“谁可以称自己为女人”。
不过,我认为榭尔丝的论述核心在今日仍十分有意义,因为,由于我们未能保护女人作为人类的人权,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要求由“雌性/女生(female)”这个概念来接管女人作为人类的政治权利/义务的环境。因为缺乏将女性视作人类(Homo)的政治范畴,“雌性/女生(female)”成了接管女人相关权利的分类。换句话说,在政治上,我们谈论关于男人身为人类(man as human)的权利及“雌性/女生(female)”的权利。
确实,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女性必须围绕着她们“雌性(femaleness)”的身份来争取人类的权利,因此,在当前这个时刻——正如布朗·杰克逊法官所指出的,“谁算是女人( Who is a woman)?”——这个问题具有深远的法律和政治影响。
但是,“谁算是女人?”这个问题对保守派来说尤其棘手:若我们极力强调以“雌性(femaleness)”的维度来定义女人,而不是强调女人们与男人共同拥有的人类属性(humanity) ,我们就会将作为公民权利源头的“人类”这个类别的意义最小化。
换句话说,如果保守派对女人的定义一开始就不包含权利的预设,那么他们在当前的辩论中就很难令人信服地声称自己是在为保护女人的权利而奋斗——对那些抵制“社会进步运动”、试图将性骚扰和性侵等指控的严重程度最小化为“只是男人们随口开的无伤大雅的玩笑”、历来反对基于性别保护女人的法律的某些保守派来说,尤其如此。
我不禁想知道,如果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确实建立了定义女人的法律先例——不是将女人定义为“一群性别相同的特殊利益群体”,而是以生理现实(biological human reality)来定义女人的人类性,今日的对话是否会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用整个世纪的时间来学会视女人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今天的对话又将如何展开?
但这些“如果⋯⋯”无法解决我们正面对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现在正努力就最核心的问题达成共识——“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之所以的样子?”。我们应如何应对当前混乱的时刻呢?
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对女人的定义有缺陷——这些定义往往不是基于“神的形象(imago Dei)”,而是基于“不是男人的任何另一种东西。”我们不需要用“人类(human)”的概念取代“雌性/女生(female)”的概念,因为这两种类别不同,一个不能取代另一个,我们两者都需要。但是,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女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为我们正是从这个类别中获得相应的权利和责任。
我们不应从《创世纪》第二章或《以弗所书》第五章展开对男人和女人的理论的研究,而应根植于《创世纪》第一章,肯定男女共同的人类属性,因为我们的差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男的人类”跟“女的人类”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但性别差异无法解释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如果在我们的次文化中,男人已成为对“人类”的预设定义,我们就必须悔改。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脆弱性。人们对性别(gender)或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的观念正在迅速改变。事实上,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不成比例的改变,必须在自己被这些改变压垮前遏制它们。虽然这个时代的改变确实来自文化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实际上目睹了“现代性”的弱点——不仅在关于性别(gender)的议题上,还有关于定义人格性(Personhood)和自我创造的限制上。
人们之间的对话正在迅速变化,就像波浪在即将抵达波峰并破碎时的迅速变化一样。榭尔丝在1942年发表的《为什么我们要工作》一文中谈到这种现象,她指出,社会有内在的自我修正周期,而这些周期往往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
那些不愿意主动修正自己观念的人,在这些观念所导致的事件的巨大压力下,才不得不改变观念。 ……冲突的根源通常源于某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因各方都默认了这种生活方式,因此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原则的领袖就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应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领袖们必须找出我们辩论的真正根源,避免让将“造成此类辩论发生”的因素永久化——这包括我们如何未能真正地重视女人的“人类(humanity)”属性。
最后,我们必须追求一种“既尊重对话者的人性(humanity),也尊重我们自己的人性” 的质疑和探究的过程。尽管你可能认为定义“谁算是女人”的答案很简单,但你的邻舍却越来越不这么认为。与所有人和平相处意味着学习以恩典和真理的态度处理这些分歧,不仅要肯定与我们持同观点的人的人性,也要肯定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的尊贵人性。
在我们所处的时刻,要做到以上这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你试图从政客汲取灵感,也是不可能的。但对于那些生命正在积极地被基督改变得更像祂生命样式的人来说,他们的人性正因着与基督的合一而得到救赎和实现,兼具恩典及真理的姿态对他们而言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汉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着有《为更多而造》(Made for More)、《美好的一切》(All That's Good)和《谦卑的根基:谦卑如何滋养你的灵魂》(Humble Roots: How Humility Grounds and Nourishes Your So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