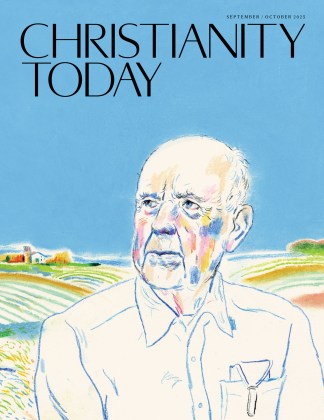我之所以成为重洗派基督徒,是因为小布希总统 (George W. Bush)。
不过,倒不是因为布希本人的关系——虽然他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发动的战争,正是我开始思考耶稣关于 “仇敌” 的教导的背景。不过,更准确地说,我成为重洗派基督徒的起因,是2000年代初期,美国福音派文化对布希及共和党的拥护。
那是个 “上帝-国家” 紧密绑在一起的年代,跟今天的氛围有点像。
我们那时并不常听到 “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 这个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神权统治”(theocracy) 或类似的变体词,而且共和党当时在若干重大议题上的立场,也与今日不同。回首过往,布希本人比起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川普,其实算是更为传统的政治人物。
但当时的气氛是这样的:福音派基督徒觉得自己在华盛顿有盟友了;“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支持哪个总统” 之类的问题简直没有第二种答案,而成为好基督徒,几乎等同于成为好美国人;在主日礼拜播放 “明确地将美国士兵的牺牲比作基督救赎性的死亡” 的影片,是完全恰当的行为——所有这些氛围,在2004年和在2024年的今天一样浓厚。
于是,当那时的我遇见重洗派 (Anabaptism)——这个今天满五百年的教会传统——时,感觉就像天上降下的启示。
我最初被重洗派吸引,是因这个信仰传统对 “政治” 和 “权力” 持深刻的质疑态度,以及他们对圣经中关于 “和平” 的命令所做的简单、顺服的理解——并且这种解读因早期重洗派基督徒的见证得以强化:他们之中许多人因信仰而被其他基督徒杀害,成了殉道者。随着时间过去,我也逐渐爱上并钦佩重洗派另一个独特的特色:极度重视基督徒群体生活的深厚连结,以及普通基督徒皆具备熟读圣经、活出信仰的要求。
在搬到一座新城市前,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学习重洗派的信仰。那次搬家让我和先生有机会加入一间重洗派教会,而这间教会后来加入并成为美国门诺会旗下的教会 (Mennonite Church USA, 简称MC USA)。
我们教会里有一些 “族裔意义上” 的门诺会基督徒——他们的家族在这个信仰传统里已传承好几代人,有些甚至与艾美许社群 (Amish) 有亲属关系。但多数会友则和我一样,都是 “布希时代的福音派” 难民,渴望找到一个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更高标准的教会。
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能以教会为中心。我们渴望过着信仰群体的生活,会友皆住在彼此附近、每周聚会多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无论是较正式的聚会,或单纯相处、一起逛街、吃饭、玩耍)。在教会的早期阶段,也就是我加入前,许多成员甚至住在共同生活的社区大房子里,一起吃饭、种种花草、分享资源。
后来随着人们开始结婚,那些共居的屋舍也逐渐解散。从这一点你大概能推测,那间教会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我这样说并非贬义;我们虽然年轻,对信仰却很认真。重洗派的信仰传统,是指引我们热忱信心的力量。
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我和先生同时参加了一个聚会小组及一个讲道讨论组。由于教会没有自己的聚会建筑物,只能在周日晚上礼拜,因此我们每周有三个晚上与教会活动有关——而我们深爱这样的生活。
然而,在教会正式加入美国门诺教会 (MC USA),在制度上成为一间名副其实的重洗派教会后不久,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教会有个问题——而且这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我们教会,就我观察,整个宗派似乎都有相似的状况。
我并不想抹黑这间对我的灵命有深远塑造及影响的教会,我至今仍有许多挚友在那里聚会。所以我只想这样说:我们在培育及实践重洗派 “深厚的信仰群体生活” 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维持早期教会对神学与圣经教导的专注上,却做得不太理想。虽然我们从未停止宣讲上帝的话语,但当宗派展开有关同性婚姻的辨识过程、意见分歧浮现时,我们才惊觉,原来我们之中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吸收重洗派传统上视圣经为 “基督徒生活最高准则” 的理解。
这种转变在我与教会几位姊妹一同前往重洗派旗舰神学院参加神学会议时更为明显。那场会议上讨论的许多主题令人费解,只有相当少的内容是重洗派传统的创始人们认得出来的。
有一场讲座令我印象极为深刻——讲者主张耶稣是跨性别者。我的一位朋友出于好奇去听,想知道这论点究竟如何成立。她回来转述说,讲者的论点是:由于耶稣没有生物学上的人类父亲,祂可能只有X染色体,但祂又是以男性形象出现,因此祂是跨性别者。当我听朋友转述这段话时,脑中不禁浮现门诺会创始人西门 (Menno Simons) 从坟墓里翻起身的画面。
尽管受到疫情的延宕,美国门诺教会 (MC USA) 最终仍投票通过,修改其关于同性婚姻的神学立场,转向支持与肯定的方向。旗下较为保守的门诺教会则多已退出MC USA,另组自己的宗派联会。
其中有些保守派门诺教会仍保留了重洗派的历史特色,但也有些正逐渐偏离该传统在 “和平” 与 “政治” 上的核心立场,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上看起来越来越像一般的福音派教会;进步派的门诺教会则同样涉入政治,而这两方人——正如我在《纽约时报》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写——都缺乏指引他们如何 “好好地参与政治” 的神学传统根基。
结果就是,如重洗派学者罗斯 (John Roth) 在《Plough》杂志中所说,双方的 “政治见证” 基本上往往 “与更广泛 (世俗) 文化中的党派二分一致”。
当然,重洗派在西方的未来,并不取决于那些随政治与文化风向摇摆的美国人。最终,一切都取决于上帝。即便从人的角度来看,旧制门诺派 (Old Order Mennonites)、艾美许人 (Amish)、布鲁德霍夫团体 (Bruderhof) 以及其他类似的传统信仰群体,依然数十年如一日、甚至数百年如ㄧ日地维持着他们的样貌。
但那种年轻时曾对我信仰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重洗派——那种既保有其独特及传统性,却又不封闭或与世隔绝的重洗派——似乎正面临危机。若像这样的重洗派式微,将会是基督信仰的极大损失。
虽然出于各种原因,我在搬到另一个州后加入了一间圣公会教会,但我仍视自己为一名重洗派基督徒。我明白,这个信仰传统的先辈们或许不会同意我这种认同,我只能说,我渴望自己能比现在的状态,更效法他们、活出他们那样的信仰。
若主容许,我盼望他们所开启的这个运动,能在下一个五百年后依然坚韧而充满生命力。我盼望其他基督徒依然有机会认识这个信仰传统,尤其是年轻人——愿他们也能被这份对基督彻底委身的榜样所激励。
Bonnie Kristian是本刊观点专栏与书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