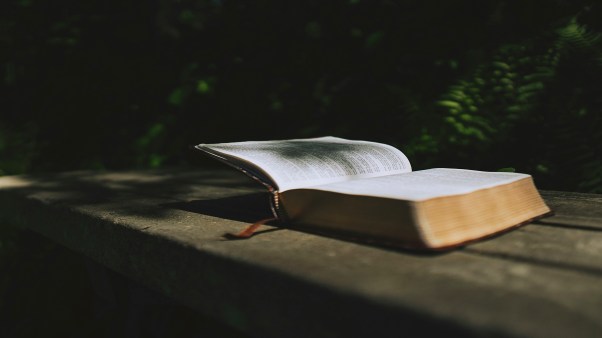身为一名宣教士,我常被问到有关 “短期宣教” 的问题:这样做有害吗?有什么地方能做得更好?当我们试图想帮助别人时,是否反而做错了?
像这样的问题,对教会而言还算新鲜事。没有多少年前,美国教会仍流行在暑假期间派青少年到某个较贫困的国家,帮忙漆教堂或陪当地孩子踢足球。但如今,许多基督徒开始反思宣教事工中的权力不对等等议题,并且提出恰当的问题: “短期宣教” 在神学上、伦理上,或实际运作上,是否真有其合理性?
有些人甚至主张应该完全取消 “短宣队” 的存在,而其中确实有值得思考的道理:试想,如果有一间非常有钱的韩国教会联络你,说要派一支短宣队到你的教会,你会怎么回答?如果突然有十几位富家青少年涌入你的社区,和你们教会幼儿园里的孩子合照,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安排什么样的工作,好让他们觉得自己 “有帮上忙” ?
我的立场还不至于到支持教会应永远淘汰 “短宣队” 的概念。但在又一个 “短宣队季节” 结束之际,我确实想从宣教士的角度,谈谈不同形式的短期宣教,以及如果你想参与短宣,该如何让它既有果效,又忠于信仰。
我们先从最糟糕的一种短宣开始:那种看起来完全就是为了Instagram (或任何社交媒体) 而设计的短宣队。这类短宣其实是一种彼此剥削。一个开发中国家的教会或事工,希望借着富有的外国人来访,吸引当地人的注意,并获得海外资金,并且他们会刻意营造一些经历,让短宣队成员觉得自己 “做得很好”。
这种类型的的短宣队可能包括 (但不限于) 安排机会让短宣成员与生活在贫困中的可爱孩子合照、制造一些 “忙碌” 的计划让 (相对而言) 富裕的青少年觉得自己有在做事,或找到一些人宣称他们在这段时间 “把生命交给了基督”,好让来访的讲员能计算一大笔 “得救的灵魂数量”。虽然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类短宣所带来的伤害,并且有减少的迹象,但我们仍时有所闻。
要避免掉入这种短宣模式,可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 你这趟旅程会不会给接待你们的人带来额外的负担?
- 你们团队所做的事,是否真的有实际帮助,还是其实只要给当地人足够资源 (如金钱),他们自己就能完成?
- 短宣队与接待的事工之间能否建立长期的关系?
- 短宣队所做的事,如何与当地事工的整体异象连结?
- 你们的服事能否带来长期推展的可能,还是长远来看只会让当地人的处境更艰难?
以我所从事的医疗宣教为例。有些手术能够改变生命,且不需要后续追踪,若没有外来专业人士,当地人根本无法完成——像这样的医疗短宣行程相对单纯,通常也很值得。但若只是由外来医疗人员分发药品,这种短宣往往不会带来长远的影响,甚至可能让当地人更不愿意投资自己的医疗基础建设。
在思考短期宣教时,特别需要注意其长期影响,尤其是关于 “依赖性” 的问题:短宣队的到来,会让接待的事工更具可持续性,还是更依赖外力?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不同事工有不同的需要。举例来说,我们多数人都理所当然地期望一间地方教会的牧者,足以靠会众的十一奉献与捐献来支领薪资,即便有些牧者会另外兼职补贴收入。另一方面,像校园事工 (例如校园团契、学园团契,美国InterVarsity) 的同工,绝不可能单靠学生的奉献来养家。换句话说,有些事工类型可以自给自足,有些事工则持续需要仰赖事奉对象以外的资金来源。
有些依赖性是合宜的,甚至必须长期如此;但有些依赖关系却可能变质,成为有害的。例如某些国家长期习惯富裕国家的援助,结果从未真正发展起自己的经济。同样的,如果一间教会逐渐依赖外国的捐款来喂养本地孤儿,而不是呼吁自己的会众承担责任——或干脆放下所有福音事工, “反正美国青少年很快就会来做”,那么这其中已经出了问题。
说到孤儿,也许短期宣教最具争议、最棘手的环节,就是他们与孤儿院的互动方式。无论基督徒或世俗的声音,都一致呼吁应该结束孤儿院的制度,因为相比在家照顾或寄养照顾,孤儿院对孩子反而更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已开发国家的孤儿院早已不复存在。孩子在孤儿院里常更容易遭受虐待,而其中不少孩子其实仍有一位或两位仍健在的父母,只是父母为了让他们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选择将他们送到孤儿院。
孤儿院之所以成为短宣的热门目的地,是因为访客在短短一周内与孤儿建立的强烈情感连结,往往能转化成持续不断的远方金钱支持。但教会应该避免这类短宣方式,转为协助现有的事工转型,走向不同的模式。
所以,以上是 “不好的短宣” 例子。那么,“好的短宣” 是什么样子呢?理想的短期宣教,应该让来访者去做当地事工无法自行完成的事,同时也帮助该事工提升自己的能力,将来能更独立地完成更多事工。这样的短宣必须发生在一段长期的互动关系之中,而不只是一次性的探访。但即便如此,对接待方来说,这样的短宣仍然需要耗费大量心力筹备 (特别是有语言隔阂时,还必须聘请翻译)。但若能以正确的方式经营双方的合作,这些祝福会在访客离开后继续延续下去。
以我所在的医疗宣教为例,较健康的互动模式是这样的:外来的医师来我们医院看诊,同时培训我们本地的医疗人员,并带来专业的医疗设备。这些来访团队既满足本地人当下立即的需求,也把技术传承给本地人,带来持久的影响。
其他来访的事工团队则采用 “培训培训者” (training of trainers) 的模式,帮助本地人学习植堂、门徒训练或福音布道的技巧,然后鼓励本地人再去装备其他人,如此一来,未来接连不断的短宣事工团队就不再是必要的。
好的短宣事工也可以为接待团队提供喘息的机会。当短宣队能分担,或至少减轻当地医院或教会同工的工作量时,例如帮忙照顾孩子或提供其他类型服事,当地同工、牧师就能休息,出差或参加研讨会,而这在平时往往难以实现。
短宣队也能扩大当地事工原本已有的成果。举例来说,一间教会可能已会定期培训当地牧者,但若有一支教师团队来访,就能让他们同时装备更多人。在我所服事的宣教医院里,我们每年都会教授学员急救技巧,而那些在这段时间来帮助我们教课、代替我们在医院查房的短宣队,让我们能更专心投入课程,成了我们极大的祝福。
我们同样很感恩那些特别用心及体贴准备的物资,从手术器材到宣教工场难以取得的 “安慰食物”,有些短宣队全包办了!他们送来一大袋美味的蔓越莓干及巧克力后,一位先生便与我们的住院医师一同进行手术,他的妻子帮忙宣教士孩子们的在家教育课程,随行的青少年则为我们举办一个小型足球营队。
虽然这类型的短宣服事不那么吸睛、不那么能 “在Instagram上获得喝彩”,但好的短宣服事依然能达成与糟糕的短宣 (虽然我们可以同理他们的动机) 相同的正面果效:它们仍能为贫困国家的事工带来资金,仍能让参与短宣队的基督徒 (尤其是年轻人) 有跨文化的经历、足以改变他们一生的信仰视野,或燃起他们长期宣教的呼召与毕生委身的愿景。
区分 “好” 与 “坏” 的短宣事工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诚实、透明地面对自己参与短宣的动机,以及短宣队与接待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的脉络。
所以,如果你想去另一个国家,亲眼看看你们教会所支持的事工实况,其实你不需要觉得自己非得 “完成” 什么事。单纯的去那里与人们建立那份关系吧,去看看你们的奉献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或者,如果你希望让你家的青少年真实体验贫穷的样貌,并看见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如何在艰难环境中仍然敬拜上帝,就坦白承认你确实希望他们拥有这样的经历。这种经历依然能是极有价值的——只是你或许不用特别称之为 “短宣”。
再或者,如果你是学生或实习生,想要跟随专业人士学习,好为履历加分,或探索宣教工场的生活样貌,你也可以坦承明白地表达这个目的。
而如果你是接待短宣队的那一方,也要坦诚表明,你希望人们来访,是为了他们回去后能为你们的事工祷告,并支持你们的事工。如果你的事工因为人们想看看 “外国人” 而成功吸引到地方民众,你也能告诉来访的短宣队,他们的存在某种程度是你事工的 “免费招牌”。
短期宣教可以是有益处的——前提是你做好充分准备,并且有智慧地反思谁会因这样的安排得益,以及具体是如何受益的。而且,除了这些提醒外,当你在规划教会明年的行程时,要知道,其实已经有许多关于短期宣教最佳实践范例的资源可供参考,尤其是医疗宣教方面。
即使我全家人如今已在海外作长期宣教士,我仍希望等我的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后,也能参与一次短宣。我希望他们能看见一个比我们现有处境更偏远、更艰难的地方,好让他们也能体验在不同处境中基督徒事奉的样貌。作为基督的身体,在这个交通与通讯极其便利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机会跨越国界彼此鼓励、彼此支持。而我们再也没有借口把这件事搞砸。
马太·罗夫特斯 (Matthew Loftus) 与家人现居肯亚,在一间宣教医院教授并从事家庭医学。他的新书《Resisting Therapy Culture: The Dangers of Pop Psychology and How the Church Can Respond》(暂译:《抗拒治疗文化:流行心理学的危险与教会的回应》) 即将由InterVarsity Pres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