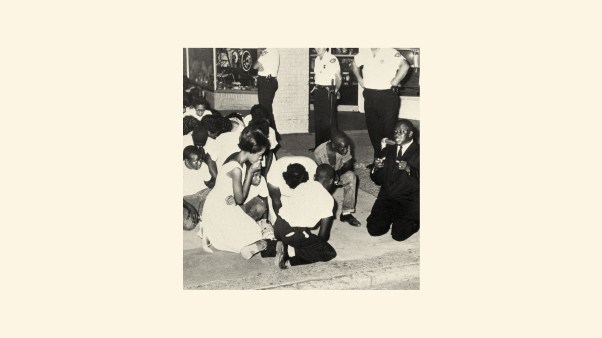2009年6月的一个黄昏,尤金 (Eugene Ooi) 正驾车前往匹兹堡大学城。绚丽的夕阳画面激起了他的灵感。
“我开始想像,这里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内心正渴望着一个……温暖又有归属感的家,即便远在他乡。”
来自马来西亚的尤金,对这种感受并不陌生——他在17岁那年来美国留学。因此,透过他的教会 “匹兹堡华人教会奥克兰堂”(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Oakland, 以下简称PCCO),尤金发起一个新的小组,取名为 “心家”,旨在向邻近几所大学 (卡内基美隆大学、匹兹堡大学和杜肯大学) 的华人留学生伸出友谊之手。
“心家” 小组成立的第一年就经历了一段令人惊奇的增长季节——“那是我们至今未曾再以同样方式经历过的一段时光,” 尤金回忆说。当时每十位新来的学生中,就有七、八位信主,许多人如今已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服事。这些华人学生渴望群体,也对基督信仰抱持兴趣。
“你可以说,这是上帝对我们全心投入校园事工的一种奖赏或印证,” 他说。
如今,尤金仍担任教会校园事工的负责人,专注服事华人留学生。然而,随着全球趋势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教会的事工模式也不得不调整。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经济背景的提升,使教会过去提供的接送服务或免费餐点等实际关怀变得不再那么有效。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对宗教的控管,越来越多学生对与美国基督徒接触抱持疑虑或恐惧。也由于取得工作签证的困难性,学生更有可能在毕业后回到中国工作和生活,而不是留在美国。
近期,特朗普政府宣布计画将 “积极地” 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就读于 “敏感学术领域” 的中国留学生签证。今年五月,美国一度暂停外籍人士申请学生签证的程序,并在一个月后恢复,但同时新增要求:所有申请者必须将个人社交媒体帐号设为 “公开”,以供政府检视。
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像PCCO这样的华人留学生事工,正在努力调整脚步,寻找新的服事方式。
“如果我们对事工方式有任何改变,那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我们渴望成长、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不断寻求与学生建立连结的更好方式。” 尤金说。
PCCO的校园团契目前在三所大学设有六个小组。团契同工Situ Junqing表示,许多参加这些小组的中国学生,今年夏天选择留在匹兹堡而没有返回中国,因为他们担心之后可能无法重新入境。美国政府近期已撤销数名卡内基美隆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的签证,并将他们遣返回国。
“现在普遍弥漫着一种不稳定的感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Situ说。
他指出,来美留学的学生往往背负着家庭的压力,因为父母在他们的教育上投入了庞大的金钱。此外,学生们也不想回去面对中国高压的职场文化,因此对于返国的可能性,在情感上是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压力真的很大,” 他说。
但Situ也看到,这正是帮助学生将他们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圣经真理上的契机,而不是建立在他们的职涯或是否能留在美国的变数上。 “我相信,这些时刻让我们能与学生同行,帮助他们将真理应用在生命中,并一起祷告,” 他说。
华人散居事工 “基督使者协会”(以下简称 “使者” ) 的主任陆尊恩表示,尽管特朗普政府曾威胁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但这不一定代表会出现大规模的政策转变。美国的大学,还有医学、工程等产业,仍然需要有才华的中国学生。“一旦某些政治或利益上的冲突解决了,情况会回归基本面,因为对这两个社会而言,合作的需求远大于竞争,” 他说。
担任门徒门徒培育资源主任的陆尊恩指出,过去十年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这一趋势在COVID-19疫情期间更加明显。但他也说,许多有抱负的中国家庭仍然希望将孩子送进美国的顶尖学府,而那些实际来到美国的学生,往往比以往更有目标,更愿意长期留在美国深造与发展。
“他们会谨慎选择学校,努力读书,规划财务,对基督信仰也有较正面的看法,对美国社会充满好奇。” 陆尊恩说, “从校园事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好消息……现在反而更容易建立真实的关系。”
匹兹堡的PCCO向学生事工成员进行一项线上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的需求。尤金 发现,最焦虑的是那些拥有H-1B工作签证或绿卡的年轻专业人士,因为他们更倾向留在美国,而许多大学部或研究所的学生则打算回中国发展。
今年夏天,尤金安排了一系列讲座,帮助学生了解当移民官上门或要求对话时,他们在美国宪法下所拥有的权利。不过,参与人数低于预期,他认为这反映出学生们对此其实并不太担忧。

“我认为,那些还没来美国、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压力比较大;但已经身处美国的学生,对现况已有一些适应,觉得还可以,” 尤金表示。
虽然团契领袖们无法确定今年秋天的政策变化会如何影响新生,但他们知道,他们仍会有机会向来自中国的新学生分享耶稣,就像他们的母会近ㄧ百年来所做的那样。
PCCO是匹兹堡华人教会所设立的植堂。该教会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当宣教士Lizzie Shaw在匹兹堡的唐人街召集13名儿童一起查经。当年,匹兹堡的钢铁工厂吸引了许多早期的华人移民,之后又有大量华人学生前来就读该市的大学。匹兹堡华人教会于1967年正式成立。
PCCO的牧者盛新光 (Steve Sheng) 指出,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校园事工一直是教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会领袖们也希望进一步强化校园团契与地方教会之间的连结。
对许多华人移民而言,大学是信仰旅程的关键时期。尤金自小在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教会长大,青少年时期参加一场青年营会时受到呼召,立志投入全时间事奉。他在乔治亚大学就读期间,积极参与学生事工,并结识妻子Meiru,他们夫妇的心也因此对中国人充满负担。
他们原以为这意味着他们将来会去中国做宣教工作,但夫妻俩于2005年搬到匹兹堡,因为尤金要在那里接受眼科住院医师训练。他们开始在PCCO聚会,并投入服事中国留学生的事工。尤金说,他们很快就意识到, “即使是在这座城市,中国学生的禾场也是何等广大”。
Situ和妻子Yin Shengjun来自上海,两人是在攻读研究所期间,在PCCO团契信主。 Situ原本来自佛教背景,在Shengjun (当时仍是女友) 与Meiru建立关系并信主后,他一度难以接受基督信仰的排他性。直到2012年,他参加一场PCCO的退修会,在一次祷告会中深刻地经历圣灵的感动。Situ哭得不能自已,并开始真正明白福音的真义。
尤金夫妇一路陪伴这对情侣,在他们经历一段艰难的分手期间持续牧养他们,也亲眼见证Situ在信仰上的真实成长。“他们真的看着我们一路成长、分手、争吵、摔门——我不知道他们家的门被我们摔了多少次,” Situ笑着说。

正因为亲身经历过校园事工对生命的深远影响,Situ夫妇后来也在工作及抚养四个孩子之余,开始带领学生。他们深信中国学生事工是全球宣教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所栽培的门徒,将来会回到中国,或前往世界其他地方。
“门徒训练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匹兹堡的教会,而是为了上帝的普世教会,” Situ说。
今年七月,校园事工团队聚集讨论如何以新的方式接触学生。Situ指出,无论是地缘政治的变化,还是世代文化的转变,都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事工策略,并在祷告中寻求方向。
“当然,上帝掌权一切事,” Situ说。 “我们只需要忠心,并在属灵与理性上都仔细思量。每当我回顾自己的生命,都会意识到,如果上帝当初任由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服事了。”
尤金指出,新一代的中国大学生所需要的,不仅是圣经教导,更需要 “一种新的连结方式”。
传统上,华人学生事工常透过举办除夕晚餐或大型布道会来接触学生。但过去十年,团契领袖们发现,学生对这类大型活动的参与意愿愈来愈低,反而当基督徒主动接近他们、与他们建立友情时,会得到更积极的回应。
“我们必须建立深刻的关系,走进他们的生命,了解他们的学业压力、情绪挣扎和人际冲突,” 他说。
这个团契依据学年设计出一个 “生命周期” 的事工模式:八月欢迎新生,九月至十二月专注于福音外展,一月到五月则进入门徒训练阶段。领袖们会在邻近学校的教会家庭家中举办聚会,也会在校园教室内举行每周例会,以增加在校园里的实体接触、陪伴。今年,他们计画参加更多由学校主办的活动,但也会举办自己的活动,例如职涯讲座或心理健康工作坊,盼望借此接触更多学生。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基督信仰在中国的成长,越来越多学生在来美留学前就已接触过基督教,有些甚至已是基督徒。不过,多数中国学生仍是在美国求学期间,第一次听见福音。
尤金善用这样的改变,安排中国基督徒学生与属灵导师配对,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带领团契在校园里的各项活动,让他们 “真正感受到归属感”。
根据卡内基美隆大学2023年官方统计,中国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8%。尤金指出,即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致来美中国学生减少几百人,仍然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等待被福音触及。
尤金表示,目前许多中国学生正面临归属感的挣扎。“美国不像他们的家,他们面对不友善的态度,也很难找到工作;但回中国发展也不像是更好的机会,” 他说。
尤金说,这正是一个让学生重新思考 “真正的家在哪里” 的契机。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让学生明白,其实还有第三条路: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而是耶稣基督,” 他说。“所以无论处境如何,我们都会继续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