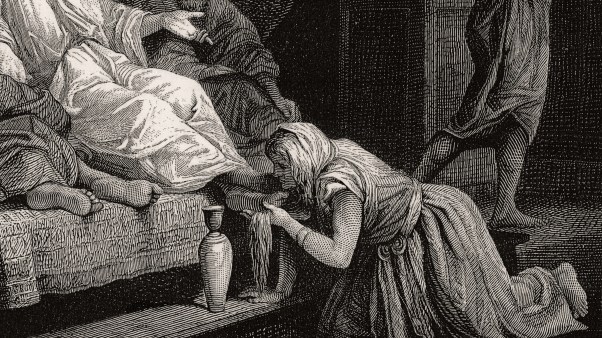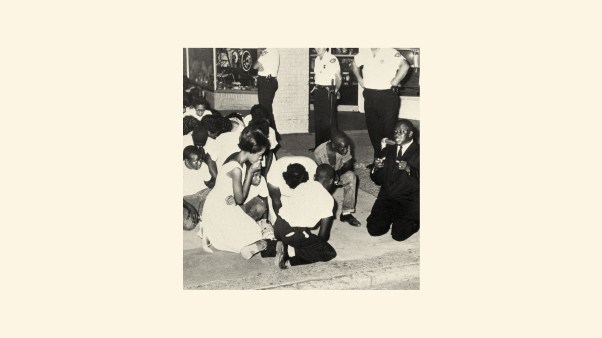史考特 (Scott Blakeman) 很喜欢看新朋友在派对或烤肉聚会上听到他随口提及自己有脑癌时的反应。
他总是像开玩笑一样,在对话深入到某个时刻时突然抛出这个讯息,精准安排,追求最佳的喜剧效果。他并不在意通常只有自己觉得这种从轻松闲聊骤然转向病痛现实的场面好笑。他甚至给自己的癌症取了个押韵绰号 (Boomer the Tumor,后来形成的小肿瘤则被戏称为baby Boomers)。
随着病情发展,史考特逐渐失去部分视力,尝试了无数种药物和放射治疗,身体变得危险地消瘦,并在短短六年内接受了六次手术。然而,史考特始终带着笑容。
而他的盼望并非表面的。他并非用笑话来掩盖、假装自己不痛苦。神学上的疑问及哀鸣同样会袭击他。他深刻地悲伤过。他知道这世界是何等地破碎、何等地被诅咒——以至于像癌症这样的疾病会出现。
但即便如此,他仍满心喜乐地爱着上帝、爱着妻子、爱着邻舍,以及爱着他的城市。
他坚决地拒绝绝望。
我不知道你通常会如何面对,但对我来说,光是感冒拖得久一点,或者一天内要回覆太多封电子邮件,都有可能让我陷入绝望。那么,我的朋友史考特是如何在面对同龄人难以想像的苦难时,依然不被绝望吞噬呢?
19世纪丹麦哲学家齐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指出,在这堕落的世界里,每个人一开始其实都处于绝望之中。或许有些人自认为没有,但那只是因为他们还没被迫去正视它。最终,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绝望。齐克果在书中透过一个代表 “基督教理想” 的化名角色论证:绝望的对立面——使人们在认清绝望后能够永久拒绝它的——是对上帝的信心。
史考特相信自己属于耶稣。他相信上帝是良善的,祂对我们的爱超乎我们所能理解。他相信死亡并非终点。他相信,总有一天,基督会使万物更新——不只是某种抽象的灵性转变,而是所有人都将身体复活,邪恶最终会被完全击败,恩典将浇灌在基督徒身上,他们将在上帝的同在中享有永恒的喜乐。
史考特的信仰给了他一种持续性的盼望。他在死荫幽谷中行走时,仍然活得丰盛且得胜。
然而,近年来,许多年轻人发现自己无法像史考特那样抗拒绝望,甚至有些人似乎根本不想抗拒。一种无望、虚无和恐惧的氛围笼罩着他们。我在此说的并非广泛的心理疾病。我自己曾经历产后忧郁和焦虑,深知荷尔蒙和身体化学失衡的影响力有多强大。我指的是,一整个世代在衡量过生命后,认为生命毫无价值,并越来越倾向于拒绝它的那种绝望。这种绝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例如,年轻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决定永远不生孩子。有人是出于经济或健康因素,但也有许多人表示,他们害怕未来只会充满无尽的气候灾难及战争,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从某种角度来看,选择自我 “消灭” 也是对这类问题的一种回答。
人类不存在,是否其实是件更好的事?
这当然是最极端的想法。但即使不是如此,许多人对未来至少是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世界的状况不可能改善。
以这角度来看,年轻人其实部分符合齐克果对所有人的预期: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罪恶、破碎世界中的绝望。然而,齐克果对绝望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对上帝的信心——并不是现代年轻人普遍采取的方向。而他们的回应也与过去那些没有选择信心,但仍试图忘却绝望、在当下环境中努力活出意义的人有所不同。
这种无法穿透的痛苦,或许可以归咎于智慧型手机和社群媒体的出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即时地接触到世界各地的苦难——也或许可以归因于他们在全球疫情与极端政治分裂的时代中成长。但我认为这些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历史上,人类见证过比这更动荡、更黑暗的时代。
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今日许多年轻人是在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相信人类只是宇宙中的一场偶然,没有特定的存在目的,也没有任何确切的归宿。等待着我们的未来,只有宇宙结束最终的热寂 (heat death)。许多人与基督教的神学根基完全脱离,使他们对抗绝望的防御力大大削弱。
他们的无望感——以及他们偶尔寻求除了齐克果所提出的 “对上帝的信心” 之外的解药 (这也是齐克果的思想继承者们最热衷的探索之一),已经显现在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当中。
其中一个例子是2022年的电影《瞬息全宇宙》。乍看之下,这是一部荒诞离奇的科幻多重宇宙冒险片,但电影所隐含的基本假设,以及其核心冲突,正反映了一整个世代疲惫不堪、无处不在的悲观主义。
片中的多重宇宙反派,在面对无穷尽的平行宇宙时,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她开始肆意破坏,只为寻找一种方式,让自己的所有版本彻底消失。而她的父母 (来自不同宇宙的版本) 试图阻止她,却无法清楚地说出她的想法究竟错在哪里。
他们最终用这句话击败她的虚无主义:“要善良。”
这是一个不错的备用准则,当一切都毫无头绪跟意义时,至少还能依靠它。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做到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所有人都保持善良”。这个答案远远无法正视罪、死亡和苦难——这些真正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依旧深深打动了年轻人,因为它映照出他们内心无法消散的虚无感,以及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渴望行善、成为好人的挣扎着。单纯为了善良而善良,或许能在这被认为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创造出某种自我构建的意义。
也许,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年轻人来说,善良本身就足以成为活下去的理由——即便一切都毫无意义。我们或许是偶然出现在这个世界,或许最终将走向虚无,但至少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伊甸园。
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仍是一种用来对抗绝望的 “信仰”,只不过,它不再依靠上帝,而是建立在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能成就的事之上。
然而,我们自身的努力永远无法带来持续性的盼望。我们或许能竭尽全力去爱他人,如同耶稣那般温柔而强烈,但如果没有祂,死亡与绝望仍会叩门而来。
圣经以清晰而充满盼望的方式,驳斥了这种最终仍是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圣经向年轻人宣告真理:生命不仅是有意义的,每个人更是无限珍贵的,因为我们是上帝按着祂的形象所造的。基督甚爱我们,在我们仍是罪人的时候,便愿意进入这个世界,为我们受苦、舍命,并最终战胜死亡,将我们从罪恶的悖逆中拯救出来。
耶稣才是对抗绝望的真正答案,远超越电影中 “要善良” 的结论。 祂以一种激进、无私、难以理解的爱来爱我们,并呼召跟随祂的人以同样的爱去爱邻舍——甚至爱仇敌。
对现代人而言,信靠上帝的最大障碍之一,与齐克果所描述的两种类型的绝望不谋而合。第一种绝望,来自于一个人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成为 “自己真实的样貌”。他们因无法摆脱的罪、身体的疾病,或来自这个堕落世界的脆弱及限制而感到绝望。他们不相信上帝能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无法想像祂真的可以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 (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类型的怀疑更为严重,人们甚至难以相信上帝真的存在。)
第二种绝望,则是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宁愿选择维持自己堕落的样貌,也不愿被祂改变,成为新造的人。
在齐克果的观点中,真正的信心是 “完全透明地扎根于上帝” 以及祂对我们的心意。
如果这样的信心是我们抗拒绝望的唯一道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像秋天的松鼠那样,拼命四处搜寻信心的橡果,好凑齐足够的 “信心存粮” 来拯救自己?我虽然很喜欢松鼠,但圣经所描绘的图像并不是这样的。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这样写道: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弗2:8-9)
在这里,我不会深入探讨上帝的主权与自由意志之间的深奥神学论战——我并不完全明白上帝的奥秘,也不想假装自己懂。 (齐克果在他的著作中,视信心为上帝的礼物,同时也是人必须踏出的行动。)
但有一点我确信无疑: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应许我们,天父 “必把好东西给求祂的人” (马太福音7:11)。当我们选择寻求祂,而非陷入绝望时,有时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像那位为儿子寻求医治的父亲一样,向耶稣呼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马可福音9:24)。这是我不断回顾,反覆向上帝恳求的祷告。
奥特伦 (Dane Ortlund) 在《柔和谦卑:基督向罪人和受苦者所存之心》一书中描绘的一个画面,帮助我更深体会我们脆弱的信心与基督之爱的关系:我们就像紧握成年人手掌的幼儿。我们或许会努力抓紧,但我们十分软弱。即使我们会分心、挣扎,双手又湿又黏 (小孩总是这样),但上帝比我们更有力,祂会紧紧抓住我们。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约翰福音10:28)
我的朋友史考特在与癌症抗争七年后,于2023年夏天去世,享年34岁。他虽渴望活下去,但他的信心同样战胜了绝望。
当他走向坟墓——也就是走向荣耀时——他紧握耶稣的手,而耶稣则握得更紧。
史考特去世后不久,数百人聚集在国会山的复活教会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为他的生命献上感恩。他们唱诗、哀悼、祷告、流泪,因回忆他过往喜欢开的老笑话而轻声笑出来,并一同纪念《启示录》21章4节的应许:“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然后,大伙们做了教会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做的事:回到城里,回到乡邻里,继续以基督的爱去爱人——在世人面前对抗绝望,并教导他人如何能如此行——直到主再来的那天。
海莉·威尔特 (Haley Byrd Wilt) 是一名母亲、记者、偶尔写科幻小说的作家。
本文最初发表于《基督教与公共生活中心》(Center for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 的2024年Journal of Ideas期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