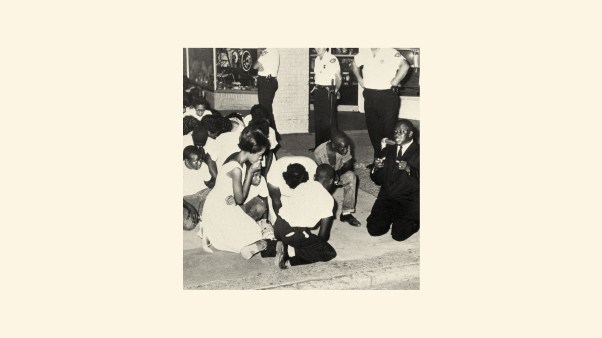去年春天一个普通的星期二,美国中西部一间福音派基督教学院的学生生活部院长对她的研究生助理——也就是我,说:“马西,我们学校的福音派文化为学生做了许多帮助 他们步入婚姻的准备,但我们很少帮助他们做好单身的准备。我们在这一点上需要做得更好。你应该来和他们聊聊这一块。你的演讲题目可以类似‘选择单身’。”
这位院长很有前瞻性,且直觉敏锐。 她下的题目背后的核心理论是:请大家重新审视我们这种基督教校园传承下来的关于单身及婚姻的假设。 这同时也是对我这一辈年轻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之中多数人至少要到27岁才会结婚,且有整整五分之一的人根本不会结婚——下达最后通牒 。
这种长期单身的趋势有几个原因。 罗伯特·沃思诺(Robert Wuthnow)和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等社会学家指出,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要求人们在传统的四年学士学位外接受更多年的教育。 许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参与志工服务或低薪的服务性质职位。 在20岁出头的时候,很少职业选择是像过去能让人萌生成家念头的朝九晚五稳定性工作。
在这种充满冒险感及雄心壮志的环境下,很少年轻人会认为“单身”是个自己需要在意或担心的状态。 当我问我28岁的朋友为什么从不参加教会为单身人士举办的任何活动时,他回答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参加。 事实上,虽然我的教会就在一间大学附近,在我们教会500名成员的名单中能列出120多名单身成年人,我们的单身事工却因人们的兴致缺缺而结束。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单身与其说是种身份的象征,不如说是人生列车为他们的青壮年时期预设的轨道。
然而,当这些年轻人到了30岁出头仍然单身时,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和上一代人在这个年纪时有哪些不同? 如果没有婚礼策划师来编排这种转变、没有仪式来宣布这种转变,他们如何冒出想要长大的渴望——学习在爱中将自己委身于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块土地? 如果没有类似婚姻的成年仪式,他们如何让社会视他们为成年人? 如果他们继续单身,拥有许多时间、金钱和人生经验,却又陷入迷惘和孤独——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的成年人?
这基本上正是我的上司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身为一位35岁的女子,从毫无计划的20初岁过渡到开始为人生做长期规划的30多岁人生阶段。 我花了半年深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 在这个倾向将婚姻和家庭视为成年人“生活模板”的福音派文化里,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单身身份?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答案是独身所呼召的“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我并非在推广回归传统上的终身独身修会生活,但我认为是时候问一句:“为什么不(独身)呢?”
我们为什么不呼召人们宣誓委身于教会呢? 如果教会重拾传统,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我们生活在“福音的首次宣告至其最终实现”之间的时间,并认知到在这段时间,婚姻是值得庆祝的事,而独身被视为对基督 及其身体忠诚的最激进的象征,那么,我们的单身文化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如果我们透过独身圣人的生命故事来补充我们的公共想像力,展现这样一种既具有目地性又令人向往的单身图像,教会的社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教会不再使用提醒着人们“缺乏什么”的相关词汇(例如:“单”身),而改为使用人们能自由选择的另一种忠诚性的相关词汇(独身),教会内的单身人士对 自己人生的看法会有什么不同?
基督徒都很熟悉马太福音19章相关的经文。 耶稣提到了“自阉的”,他们“为天国的缘故,放弃婚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提到没有嫁娶的人,说他们维持未婚 “若常像我就好 ”,并且,保罗认为单身/不在婚姻内的人“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福音派牧师们偶尔会用这些经文为独身“辩护”,却很少视其 为一种人们“应能”追求的呼召来推广。 因此,我不得不从重新认识独身生活开始。
美国教会常常会透过语言和视觉文化将“美国式的家庭梦”当作成熟的成年人的标志传递给我们——首先出现的画面是一场婚礼,然后是衣着整齐、笑容满面的家庭照(父 、母及孩子们)。
我描述这个画面只是为了重申罗德尼·克拉普在《十字路口的家庭》一书中提出的警告。 克拉普说,福音派传统所传递的家庭形象并不符合圣经教导,而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感性的庇护所——旨在让“像这样的家庭形象”成为其成员的避风港、绿洲、情感 稳定器和心灵充电器。 克拉普并不否认上帝为着人类的好处而设计家庭,并且家庭的一部分功能/益处确实如以上所述,但当这些价值本身“变成我们的目的”时,基督教对家庭的想像力就太渺小了 。 就像单身一样,家庭变成一个自成一体的躯体——单独“为了你自己的人生”而存在。
一个谦卑的提议
克拉普在1993年提出,对于家庭的想像,我们福音派需要恢复的画面是“教会身为我们第一个家庭”的画面。 他写道:“随着基督国度的来临(这个国度既存在于肉体上也存在于精神上、既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个人身上、既存在于现在也将在未来显现出来),耶稣创造了一个‘由跟随者组成的大家庭’,而这个家庭要求人们首先效忠于它。”
在基督里,保罗为自己的单身提供一个叙事框架。 保罗称自己为独身主义者。 出于对教会使命的热爱,他从不逃避重责大任。 他不是“因为⋯⋯”而单身,也不是一个人独自单身。 相反的,保罗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人,可以温暖所有人的人,他将人们团结在一起,使人们成为他的母亲、兄弟、姊妹和儿子。 随着着保罗提出的这种“超越性的家庭在基督王国里的实践”发展而来的正是教会传统上的独身主义(celibacy)。
因着对“教会作为基督徒第一个家庭”的理解,独身及婚姻同为某种呼召性的实践在教会内并存已有两千年,这种叙事比个人的益处、比美国梦/福音 派家庭美梦更广阔及持久。
14世纪英国女隐士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写道:“这是良善的上帝向一位敬虔的女性展现的愿景⋯⋯在这愿景里有许多安慰的话语,对所有渴望 成为基督的爱人的人来说都非常感动。”她的简易住所设计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同时如同她对生活的设计:白天,她祷告数小时;在祷告之间,她在住所敞开的门前 ,与巷子里路过的商人交流资讯、谈笑、咨商,以及一同祷告。
去年夏天,我在家里厨房柜子前读着朱利安的灵修回忆录,我公寓的西窗面向校园的人行道,后门则朝向我的教会。 在朱利安的独身生活中,我看到了自己其实已经爱上并享受于其中的画面。
结果,我最后未曾对学生们发表过题为“选择单身”的演讲。 但我还是在我的教会里主持一些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 在系列讨论的中途,我和我最要好的单身朋友一起吃午餐。 在聊完这堂课的氛围多么有活力后,我转向她问道:“你如何看待你的单身身份?
我的朋友并不消极。 她是位艺术家,她是位领袖,她的眼里总带着看透世界的智慧。 但这一次,她的眼睛低垂着。 当她抬起头时,泪水滑过眼眶。 她说,“我想结婚”,然后又低下了头。
我深信,多数福音派教会面对单身所采取的被动或消极的态度,是因为缺乏某种元素以至于无法热切的委身,但解决方法并不是将实际上很困难的事浪漫化。
自保罗时代以来,教会的独身传统中确实曾出现过愚昧和过激的行为。 我并不想在试图拆毁《新娘杂志》所建构的虚假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神话的同时,用另一个披着属灵外皮的虚假且过度理想化形象来取代它。
我们独身,但我们也是人。 我们结婚了,但我们也是人。 基督徒的叙事为这两种状态增添喜悦,这一点很吸引人,但它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仍然渴望更多爱。 我朋友的诚实回答让我的胜利之音戛然而止,同时也提醒我,独身群体最大的见证可能正是其“没有解答”的解答。
在天主教传统中,当修士候选人被带到主教面前 宣誓保持独身,献身于基督和教会时,主教会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再三慎重考虑,你们主动承担的是什么样的重担。在这之前,你们是自由的。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仍可以转而追求属世的目标和欲望。但是,你们一旦接受这一 呼召,就不能再背离你们的目标了。你们必须继续服事上帝,在祂的帮助下坚守贞洁,永恒地在圣坛上服事那位统管万有的。”
今日的独身主义
这种正式的独身誓言所提出的条件既令人恐惧,又充满吸引力——奇怪的是,这些条件与婚姻所提出的条件并无不同。 贞洁约束已婚夫妇只与彼此共享亲密关系,对单身者则是放弃性关系,这两种呼召都是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也都源自对爱和信仰的委身、承诺。
尽管如此,独身并不非得是终身的使命。 上帝当然可以呼召一个单身成年人以新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但前提是他或她首先健康地拥有先前的身份(独身)。 换句话说,当婚姻的呼召是由两个首先知道自己是独身者(在主里完整)的人接受时,我们对婚姻作为神圣呼召的认知——正如圣公会仪式手册所说的那样 ,这种呼召的“不可轻易接受性”就会展现得最为强烈。
虽然有些教会可能会对举行独身誓约仪式感到退缩,但我们仍可以改为使用“独身”这个词来正确地称呼单身人士目前被呼召要活出的这种反文化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仅仅只是在鼓励人们“不要发生性行为”,我们是在祝福“单身/独身”身为一种使命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回顾教会历史,我们会想起我们真正的家庭是教会,我们视单身人士为主所呼召的人,他们和已婚的人一样有家庭的恩赐——并有使教会(上帝的家) 成长的使命。
要让我们的教会回到欢迎独身主义的文化,可能仅仅只需单身的基督徒们展现他们美好的独身生活能如何成为教会共同体的帮助。 读过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灵修回忆录《爵士乐之蓝》(Blue Like Jazz)的人,都会在他对酒馆、咖啡馆、大学校园和面包车的描述里听到像这样一位独身者 的故事:他像圣方济各那样,赤着脚,行动自如,在每个他所接触的人身上都能见到耶稣的面容。
像米勒这样的还有如肖恩·克莱伯恩(Shane Claiborne)这样的年轻人,他在费城建立的“简单之路”社区为一个由已婚夫妇和单身人士共同组成的致力于贫穷、 贞洁和顺服的社区生活模式——这是一种首先由初代教会建立的模式,后来圣本笃再更有次序的组织这样的社区/共同体为修道院。
单身并非社会里反常的现象,独身对我们来说也不应该是这样。 在后现代文化里,我们也有像德蕾莎修女和新修道运动这样将独身的神圣挑战带到教会面前的前辈。
教会的机会就在于承认现况:受过高等教育、有创造力、有企业家精神、灵命活跃、愿意投入在有着传统根基的呼召的年轻人数量的激增——他们就像照亮了《凯 尔书卷》,有效地将这份圣经传世文本保存下来的修道士一样;或像亚他那修(Athanasius)这样的初代教父、玛格丽娜(Macrina)这样的教会母亲、阿奎那(Aquinas )这样的神学家、德雷莎修女(Teresa of Avila)这样的关怀者,以及沙漠修士这样的圣贤。
“单身”一词不足以形容他们的身份——这些圣人的智慧促使他们将自己的情感融进教会这个不断向前行的大家庭里。 而“独身”这个词让我们知道,这些人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特意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将他们的社区/共同体深深放在心上。
教会——是个透过彼此的生命来诠释自己人生的共同体(community),我们不断地互相映照着我们在上帝国度叙事中的角色。 在恢复教会里关于“独身”的词汇时,我们将恢复这个在历史上“生养了众多生命”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恢复基督论里所讲述的家庭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独身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一种值得委身且神圣的关系。
马西·欣茨(Marcy Hintz)是伊利诺州格伦埃林复活教会(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in Glen Ellyn)的成员,也是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研究生院基督教培育与事工课程的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