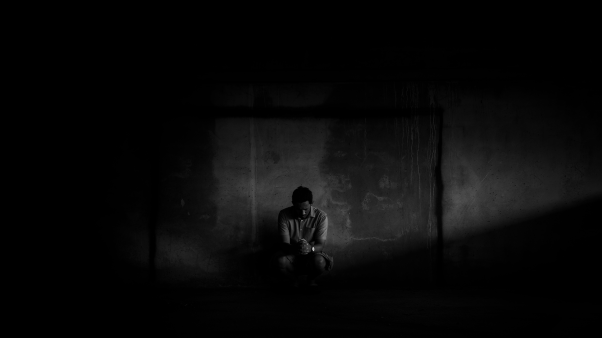他的妻子在花园里发现了他。但妻子无法把他摇醒。
急救人员赶到后,他们将一根管子插进他的气管,把空气打入肺中帮助他呼吸。他的肺早已满是长年抽烟和当年军中的火药所造成的伤害。多数的人都需要先被麻醉才能忍受插管的过程,然而,他既没有咳嗽,也没有退缩,更没有呕吐。如此平静的反应是不祥的征兆。虽然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但他的大脑已陷入了沉寂。
在急诊室里,电脑断层扫描证实了是动脉瘤破裂。血液从他的脑浆中涌出,顺着脑壳底部狭窄的缝隙往下流。持续增加的压力使他的大脑几乎窒息。
我在重症加护病房(ICU)的会议室见到他的儿子。波士顿天空灿烂的星光编织出的夜景正展现在他身后的窗户。他面对着我,双臂交叉在胸前,下巴紧绷着。他那被机油弄脏的拇指和食指不时拉扯着自己的运动衫,透露着他的心痛。
我解释了他的父亲快要死了。我们救不了他。
“我们现在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确保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有最舒适的环境,跟他所爱的人陪伴在身旁。”
他默默地盯着地板。 “不,”他终于小声说。然后,更大声地说:“不。不可以这样做。爸爸是个斗士。他人生每ㄧ天都会祷告。而且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目光相会时,愤怒使他的眼神变得坚硬。 “请继续抢救他。”
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在加护病房里,深深地刺进我们对神的理解和与祂的关系的核心。亲人们在伤恸、怀疑、恐惧、愤怒,甚至内疚的情绪里,在充满母亲的声音、父亲的笑声或孩子的咯咯声等各样复杂声音的环绕下深深纠结着。医生们同样纠结于区分他们的抢救措施是挽救了生命还是延长了痛苦。护士们强忍着眼泪,看着他们的病患每一次翻身、每一次换药、每一次打针时脸上痛苦的表情。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我们的心在哭泣(诗篇13:1)。
尽管现代医疗系统处在面对最基本的灵性问题——生与死——的最前线,但在信实的回应上,它们却缴了白卷。专业医疗人员在这样的困境下会咨询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而不是圣经。我们恳求安宁照护专家的帮助,紧抓着“病人有自主权”和“有品质的活着”等心灵鸡汤。我们身穿平整的医师袍,专注地讨论心肺复苏和喂食管等问题,并握着对方的手,同情地倾听对方,然后问:“你的亲人会想要什么样决定?”
“神的旨意是什么?”——虽然平时听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很困扰——但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出现在加护病房的会议室。医院提供的院牧服务只能带来极微小的安慰,然后我们把“为病人做决定”的重担交给他们的亲人,而不是和他们一起将病患交托仰望于主。
对人们身体的照护和心灵照护间巨大的断层让身为医护人员的我们心神不安,毕竟死亡在医院发生如此频繁。罗伯特·威尔斯(Robert Wells)在他的《面对“恐惧之王”》一书中写道,在1908年,有86%的美国人在家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例已下降至20%。根据疾病管制中心的数据,在我们这个重症护理高科技化的时代,有25% 65岁以上的病人死于加护病房。死亡已从有家人、牧师陪伴的宁静住家,转移至有警铃装置的无菌病房。
医院里的世俗社会处境能让已在绝望和不确定里挣扎的基督徒失去方向。一个装备妥善、以基督为中心的临终关怀方式,需要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度、理解病情发展的方式,以及对生命维持措施的目的和局限性有一定的知识。我们的目标应是让那些面临生命终点的人有着平安和分辨力,并确保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顾病人。智慧始于神的话语,这个真理在医院的处境下依然适用。
世人生命的神圣性
基督徒反对堕胎和所谓的“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例如安乐死)”等高度被政治化的议题,是基于我们视生命为神所赐的礼物。圣经教导我们,人的生命具有基本的价值,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管理祂的创造物及服事祂。 (创世记1:26; 2:19-20)。祂也教导我们要保护和珍惜生命。此外,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哥林多前书9:19-20)。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里的工作,我们生命的最终所有权属于祂。
上帝把人的生命托付给我们,嘱咐我们要珍惜生命。就广义层面而言,我们应该提供并接受能维持生命的药物治疗,因它们有治愈我们的可能性。
生命的神圣性和死亡的必然性并不互相矛盾。但当我们不计一切的代价反抗死亡时,我们也同样错了。 “我知道她快死了,但我希望你继续用呼吸器,因为我在等上帝行神迹,”病患的亲人们常这样跟我说。虽然这样的要求出于真诚的信心,但这种想法确实误导了我们,并没有反映出圣经里真正的教导。上帝不需要呼吸器就能行神迹。更重要的是,虽然上帝憎恶死亡,但死亡是罪必然的结果。罪对我们属世生命的影响力超越我们所能做的。在上帝的主权中,祂决定了我们死亡的方式和时间。即使是战胜了死亡的基督,也因顺服天父而接受死亡的苦(马太福音26:36-45)。当我们转头不愿面对自己生命的必死性时,我们把上帝贬低如自己想像出来的瓶子里的精灵,而不是万物之主,不接受“祂的心意是完美的”这个真理;我们说服自己,如果我们够敬虔的祷告,祂会屈服于我们的意志。
生命的神圣性和死亡的必然性并不互相矛盾。
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必害怕死亡。基督的复活向我们保证,“死被胜吞灭”(哥林多前书15:54-55)。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大,祂的牺牲是如此伟大震撼人心,没有什么能把我们从祂手中夺去。即使我们身处苦难时,我们也因“死亡已永远失去对我们的掌控”这个真理而欢欣。我们细尝肉身复活的应许,以及与基督永远同在的盼望。虽然上帝指示我们要敬重祂所创造的生命,但祂也命定了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终会结束。
是挽救生命还是延长痛苦?
神呼召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去服事受压迫和困苦的人(弥迦书6:8)。虽然仁慈并不能作为执行安乐死(用有毒的药物来加速死亡)的正当理由,但它确实指引了我们应避免侵入性、不舒服的抢救生命的措施(若抢救措施已是多余的尝试时)。当我们为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时,我们就违背了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上帝对我们减轻他人痛苦的呼吁成了连结生命的神圣性及不可避免的死亡之间的桥梁。
扎根于圣经原则的临终关怀方式要求我们尽力寻求医治的可能性,但同样要求我们在死亡已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时结受它,并尽我们全力去减轻病人的痛苦。若要区分这两种情况——确实,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复杂纠结——取决于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生命维持系统是在挽救这个生命,还是只是在推延死亡的时间?”
医疗技术虽然复杂,但仍是人手所造的,因此并不完美。生命维持系统只是支持性的,不是治疗性的。医生把空气打入肺里,用特效药物收缩血管,在肾脏衰竭时过滤血液,迫使心跳加快,在一些实验案例中甚至能跳过肝的功能。但这些方法都无法治愈疾病。只不过是在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维持生命的医疗旨在维持身体器官功能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有机会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因。在处理感染的蔓延、阻塞的冠状动脉血管或中风时,医生使用这些技术来支撑病患。如果引发疾病的原因是可以治疗的,那么生命维持系统确实是能“挽救生命的”,因为它们能维持身体运作系统直到病人有能力恢复。然而,如果疾病的根源是不可逆转的,生命维持系统只不过是延长了死亡的过程。
上帝呼召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去帮助受苦的人。而维持生命的技术有时却会无可避免地造成痛苦。资料显示,在重症疾病中活下来的病人有很高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发病率。心肺复苏术(CPR)是一种按压胸腔的急救技术,医护人员藉由体重执行时,或如电视演员在示范时,都有可能压断肋骨。接受机械通气(mechanical ventilation)的患者往往会产生恐慌、焦虑和窒息的恐惧。长期缠绵病榻的病患会出现关节组织损坏,造成挛缩,即便是简单的翻身也会引起疼痛。
对康复的盼望,以及因此而生的生命维持系统,是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理由。然而,若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这些干预措施反而成了残酷的手段。医生和普通人面临的挑战是,要能辨识什么时候医疗行为已从挽救生命的努力变成推延死亡及痛苦的过程。
邀请基督来到病床边
对医师的训练着重在培养客观性,因此只有少数医护人员会主动开启灵性相关的对话。然而,向病人的照护团队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问题,至少能帮他们辨别病人的情况是在生与死光谱间的哪个点上:
- 现在威胁着我亲人性命的情况是什么?
- 为什么这个情况会危及性命?
- 康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 我亲人之前的医疗情况对他/她康复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
- 目前使用的医疗方法有效吗?
- 现有的医疗方法是否会增加患者的痛苦,成效却甚微?
有些疾病对病人的伤害是如此大,其死亡的肯定性对所有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而更常见的情况是,病人的状态起伏不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症有好转或恶化的两种可能性,因此,家人们和医护团队都应定期地回顾以上这些问题。此外,若有人怀疑主治医师的评估,他们有权力去寻求另一位医师的意见。
在面对临终病床前的挑战时,最重要的是能慎重熟思并迫切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清晰的思路。悲伤、愤怒和焦虑会模糊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同理心/爱心必须引导我们做决定的过程,我们的灵魂也必须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只有这样,当苦难迫使我们进入加护病房的会议室,面对我们亲人生命的有限性时,我们才能彼此服事。
凯瑟琳·巴特勒(Kathryn Butler),医学博士,是一名创伤和重症外科医生,她最近辞去临床医师的工作,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她的孩子。她在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任教,并在外科重症医护和医学教育方面发表研究报告。她和家人住在波士顿北部的郊区。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