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3 月5 日,当64 岁的曹三强牧师从缅甸佤邦越境返回中国时,中国官员正等着逮捕他。多年来,他从云南省穿过漏洞百出的边境,来到贫困的佤邦,在那里创办20 多间学校,建立戒毒中心,并向当地人提供医疗药品、书籍、学习用品和圣经。佤邦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冰毒生产地之一。
然而,云南法院却以“组织非法越境”的罪名判处曹三强七年有期徒刑。
曹牧师的案件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因为曹牧师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美国公民,曹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虽然他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但曹决定保留他的中国护照,这样他就可以回到中国服事。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牧养一间华人教会,同时训练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动员他们参与宣教。
多年以来,许多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和美国议员不停止呼吁释放曹牧师。 2019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得出结论,曹三强因信仰基督教而成为目标。
中国当局于3月5日因刑满释放曹牧师。四名警察将他押送回老家长沙,在那里,他将接受当地政府为期五年的监管和“思想改造”。
《今日基督教》采访曹三强牧师,谈及他在监狱中的生活、支撑着他的圣经经文、他对迫害的看法,以及被释放到一个已经改变了的中国的感受。(本访谈长度已经编辑)
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已经获得自由40多天了。我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的耳鸣一开始很严重,现在好多了。每天我都出去慢跑20分钟,所以身体恢复得很好。
您现在有多大的自由?
虽然司法办公室和派出所每个月仍会到我家对我进行监视,但我基本上是自由的。我可以外出,不会被跟踪。不过,我没有中国身份证,所以不能去看医生或去其他地方旅行。
您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曾在两间监狱服刑。因为我在第一所监狱(云南孟连看守所)与其他囚犯分享福音,2019年我被转到昆明监狱。为了惩罚我,我被禁止与其他囚犯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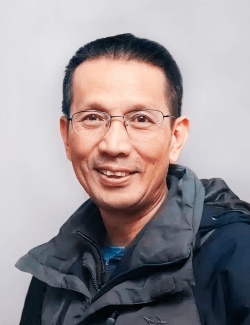 Courtesy of China Aid / Edits by CT
Courtesy of China Aid / Edits by CT在中国,囚犯需要经历劳改,即“劳动改造”。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劳动,要求囚犯长时间劳动。劳动改造的目的是把坏人变成好人。
在孟连看守所,我们缝制裤子和衣服,收入十分微薄。在昆明监狱,我组装茶叶纸袋、礼物袋和水果袋,但没有报酬。
在狱中,我没有机会晒太阳,一年大概只见过10次太阳。没有阳光和阳光所产生的维生素D,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我被禁止外出或运动。我什至不能在房间里运动。
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我们必须收看国家新闻节目。我对新闻毫无兴趣,因为这里的新闻对我而言充满教义(共产党教义),毫无意义。通常在播放新闻时,我都会低头祷告。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了解COVID-19疫情情况和其他重大外部新闻。
为了“继承红色基因,准备解放全人类”,我们所有人都要学几十首“红歌(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
由于在昆明监狱的时候,我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所以我会祷告和唱赞美诗。我也会写一些赞美诗。我被四名狱友监视着,不能走出我的房间。虽然他们可以自由地与其他牢房的囚犯交流,但我不能与他们任何人说话。同样的,囚犯们一旦看到四名看守站在我身边,也不会靠近我。
有没有特别鼓励你的圣经经文?
我在监狱中没有圣经。虽然我的母亲和律师曾把圣经带到监狱,但管教人员拒绝把圣经交给我。我母亲会在给我的信中写下圣经经文。然而,警察会检查我们的通信:如果我在信中提到信仰,他们就不会把信交给我。
两所监狱都有小型图书馆,藏书数百册。我会寻找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书,因为他的书中有一些圣经经文。找到后,我会非常非常高兴,把经文抄在笔记本上。在那里的四年,我抄写了几十节经文。
我特别喜欢那些记念在监狱中受苦的信徒的经文。诗篇137:1-3写道,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这些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在巴比伦流亡期间的悲痛经文让我感触很深。
你是否曾怀疑过自己的信仰,或想过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考验?
我未曾怀疑过。当我回到中国传福音时,我知道我迟早会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耶稣说,我们将经历祂所经历的一切。凡追求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此外,我去过中国每一个省,拜访过许多被逼迫、殴打和监禁的基督徒。我听过他们的见证。因此,当这一天来临时,我心中非常平安。我知道我会为我的信仰付出代价,所以我感到非常喜乐。
您的母亲不辞辛苦地来看你。是什么给予她力量和勇气?
我母亲看似是名普通的基督徒,但她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她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赶到孟连关押我的拘留所,很多时候她甚至见不到我。在能够见面的日子里,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窗通电话。我们的通话受到监控。
有一次,我母亲提到一位信徒转达他的问候,说他为我祷告。她的话还没说完,“祷告”这个关键字引发警察的注意,他们切断谈话,结束我们的会面。为了和我进行三分钟的谈话,她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这让她泪流满面。
根据中国监狱法,囚犯有权写信给亲人,但我只能写信给母亲。这切断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因为我只能透过她进行交流。
我写了一首诗来悼念我的母亲。我讲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母亲送儿子上前线打仗。其中一句是:昔日母亲送子去,今朝母亲与我并肩站。我视母亲为我的战友,她与我并肩作战。她比二战时期的母亲更伟大。
从当地基督徒到美国政府官员,许多人都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你,并为你祷告。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非常感谢世界各地所有为我祷告及为我奔走的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他们透过多种管道试图说服中国承认错误并释放我。
我非常感谢美国的许多立法者和官员,他们为释放我付出很多努力。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官员,他们都出于正义感为我说话。
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曾到监狱门口为我祷告。这可能会让他们被捕,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监狱的警察知道,如果有人站在门口,就是在为我祷告。一位警官曾秘密通知我,有人跪在门口为我的自由祷告。
出狱后,你回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基督徒的自由更少了,经济不断恶化,公民社会受到压迫。你是如何应对的?
最初,当我得知自己被判处七年徒刑时,我无法理解他们出于什么理由会迫害我,因为我在缅北做的事对中国的形象有益。
当我获释后,我才意识到许多牧师都被逮捕了。我意识到这是对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镇压,而我恰好是第一批被捕的人之一。
中国基督徒并不反政府,他们遵守宪法。一个普通公民都没有枪,他怎么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政府镇压基督徒,是一种自残自损的行为。不仅基督徒受到伤害,政府的声誉也会受到损害,在外名誉扫地。
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画?
首先,我想获得一个中国身份证,这样我就可以与我在美国的家人团聚。没有身份证,我就不能自由行动到其他地方,不能买手机、不能在网路上注册帐户,也不能看病。
这不仅关乎团聚,也关乎不便利性。身份证是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体现。我非常重视身为中国公民的权利,被剥夺这样的权利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类似的事。
除此之外,我的生活还不错。长沙也不错。我可以参加现场和线上教会聚会。有家庭教会与我联系,邀请我去牧养他们,但我还没有做出决定,因为家庭教会在中国仍被认为是非法的。一如既往,我的主要目的是分享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