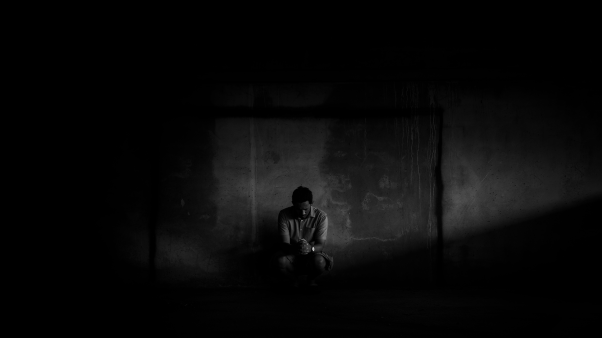几年前,改革宗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为“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下了一个实用的定义。他指出,在学术环境中,原教旨主义者基本上是个污辱人的词,有点类似⋯⋯(普兰丁格用了一个我不能写在这里的词)我举个例子吧,类似“蠢蛋”。
当然,除了羞辱人的意思外,普兰丁格认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意思是,“从神学角度来说,我和我的开明朋友们相当偏右”。 因此,学者、记者和许多基督徒开始用这个词来形容所有“神学观点跟自己相较之下,相当偏右的蠢蛋”。 但由于总是有人比自己更靠右边,所以“蠢蛋、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词的定义基本上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参考物,但反正说的绝对不是我自己。
如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评价“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 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实质内容,变成相对性的词。 几乎在所有谈话中,这个词跟“原教旨主义者”一样,除了指那些“政见与我大相径庭的蠢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意思了。 “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标签几乎可以贴在任何事上:也许它指控的人是个名副其实的纳粹。也许它指的是ㄧ个非常关心堕胎及税收议题、终身支持共和党的人。
最近,一些有想法、有善意的人努力以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定义“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汇。 但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淘汰它,再也不提到它。 虽然它曾经对特定群体和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现在已经不再适用了;这个词汇剩下的只有面红耳赤的争论,没有光。 甚至多数时候,这个词汇都是被用于诽谤他人,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人们使用这个词来与人划清界限。
确实,有时我们需要的正是界线。 我不会给优生论者或否认犹太大屠杀真实存在的人一个公平的听证会。 但这些都是边缘极端的情况,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中,公共讨论的本质是粗暴的、多元的,偶尔会令人不舒服。我们需要倾听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尤其当我们不同的程度很深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致力于热情待人和爱敌人的基督徒,我们倾听的意愿应该要更强烈。
此外,所有有责任感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反对者”——那些没有鲁莽地把这标签贴在所有比自己右边一点的蠢蛋身上的人——对这个词汇都有合理的担忧。 我认为有至少五点担忧。
首先,基督教民族主义往往带有一个修饰词:白人。
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抨击,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如此。但请注意它令人担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民族主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种族主义。任何透过社会地位提升或透过政治特权使一个种族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来作为其定义的政治运动,都值得我们谴责,无可辩驳。
其次,反对者对基督教民族主义不受法律约束的行径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2021 年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典型例子。
有时,不受法律约束意味着不愿意遵守规则。 有时,不受法律约束意味着拒绝接受政治上的失败。有时,它意味着诉诸暴力。 除了基督徒出于公义的理由而参与的无暴力的公民不服从外,基督教民族主义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展现形式应被所有基督徒谴责(罗马书第12-13章皆与此有关)。 在美国首都发动宗教政变的想法应在萌生之际就被基督徒斩断。
第三,批评者通常担心的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而是阴谋论和煽动恐惧。
小说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认为,恐惧“不是基督徒的思考习惯”。 她说得没错。 基督徒可以合理地辩论这个世界和我们国家的现状,但我们无法合理地辩论基督在这个国家的主权或再临的盼望(提多书2:11-15)。 即使我们最恐惧的事情成真了——我们被某个禁止我们敬拜上帝的政权征服,和教会历史上以及今日许多基督徒的处境一样——我们的呼召也是一样的:数算代价, 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至髑髅地。
第四,ㄧ些倡导要“把美国基督教化”的人似乎为非基督徒预设了一种次等公民的地位。
此时,那些恐惧被穆斯林或世俗世界“奴役”的基督徒试图扭转局势,反身让基督徒身份成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 有时,他们会把圣经包装成一种管理文件,与宪法同等地位,或什至取代宪法。我承认,我怀疑是否真有大量的美国人真心希望这种事成真,就像我尚未遇到一个真的支持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人一样。 如果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学者将他们的抨击范围局限在这类支持神权统治的人身上,他们的目标便是正确的——只是我怀疑这样的目标会小很多。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批评者非常正确地反对将上述几点——种族主义、不守法规、制造恐惧、不公义的行为——披上基督教信仰的语言和符号的外衣( 宣称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基督教教义”)。
这种将基督降低至自己在世俗生活得到益处的手段非常普遍,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腓1:15-18)。 这种做法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基督的名;这种做法宣称基督是所有人必须服从的主,同时却把祂的生命样式和教导放在一边。 它将圣灵所结的果子视为软弱无能,却将肉体的作为——敌意、纷争、忿怒、不和、放荡和党派纷争——视为策略资产(加5:19-23)。
如果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内容仅仅包含以上这五个问题——成为“对福音的罪恶扭曲”这种行为的代名词,我可能不会建议我们取消这个词。 但还有一些与上述无关、不应该被归类在基督教民族主义之下的正当政治参与。
以下是应该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标签脱钩的六种信仰实践。
1. 将上帝带入政治之中。 这一点我们能容易做到。 在美国,我们欢迎所有信仰或无信仰的人将他们最深刻的信念带入公共领域。 没有人需要假装。 无论是基督徒、犹太人或穆斯林,将信仰带入民主辩论及对话的舞台上,在道德上、神学上或宪法上都没有错。
2. 将政治带入教会里。 这一点比较棘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福音所公开宣称的内容与圣所围墙外的世界有关。 这些主张涉及基督对万国的主权统治,以及祂对穷人、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爱及关怀(路加福音6:20-26;马太福音25:31-46)。 对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的敬拜永远不可能真正与政治脱离——即使是艾美许派的分离主义和其他和平派教会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动。
3. 支持基督徒候选人竞选公职。 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比渴望在民主集会中拥有代表权更自然的事了。 基督徒并不是唯一希望投票给与我们信仰相同的人的人,这种倾向并不值得担心。 有些基督徒只投票给基督徒同胞,这可能是不明智的——若这已经变成不容商量的标准,我觉得很不明智——但这还不至于上升到政治病态的程度。
4. 相信上帝带领着美国。 从微观的意义上讲,所有基督徒都相信这一点(上帝的权柄超越世上所有君王),而当无特定宗教背景的媒体对“天意”等相关的词汇反应过度时,单纯只是他们反应过度。 但确实有许多基督徒赞同一种更强烈的说法:他们说美国是世界之光,是那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在上帝对世界的计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但我希望基督徒同胞放弃这种信念。 这个信念所宣称的内容实在太多了,这种宣称忽视了教会的存在、忘记了以色列的教训(罗11:1-2, 28-29)、过度将目光聚集在一个国家身上,而这个国家 和其他国家一样,终有一天会消逝(赛40:15;马太福音24:35)。 然而,实在没有什么比美国例外论还更美国的想法了。 从建国开始,这种信念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往往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在这个问题上与我意见相左的基督徒通常不是激进的右派分子,而是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人(尤其以老一辈和移民的标准来看),即使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他们也不应被以如此贬义的方式贴上标签。
5. 相信美国“是”或“应该是”基督教国家。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所记录的,与美国例外论一样,不正式的形容“属于基督教的美国”的概念也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之中。 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最近在《第一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基督教文化一直是美国的共识基础”,而这一基础在今天既可以恢复,也应该恢复 。
霍利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 但他的论点并非在呼吁基督教神权统治,甚至不是呼吁建立像英国那样的国家教会,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主张“属于基督教的美国”是合理的公共讨论范围。 它与主张“美国应是世俗的”的论点一样,都是美国式的。 这两种公共讨论的意见都值得一听。 两者都不荒谬,也不应被轻视。
6. 怀疑自由主义、民主或美国秩序。 好了,这一点是极大的症结所在。 也许特别有爱心的读者可以接受前五点,认为这是美国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不极端的观点。 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公开表示不支持自由,对民主持怀疑态度,或对整个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架构持不确定的态度。 难道他们这种想法没有太越界吗? 这种人不危险吗?难道我们不应用特殊的词汇来形容“这类人”,并且这个词应该要能强烈地表达我们的不赞同吗?
也许吧。 但请听我分享我的理由。
基督徒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是以一种近视的“历史终结”的心态来进行的。 它无视基督教大部分的历史,并视自由民主为人类社会和政治安排的“最终形式”。 在这种观点看来,我们正处于漫长进步过程的最后阶段。 我们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只能保持自己的卓越。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 教会能够并且将会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存活,历史的终结不是21世纪初的美国,而是基督的再来。 政治更迭、政府兴衰、地图重绘,在耶稣再次显现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历史已经终结。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值得珍惜或保护的东西。 但是,把现在的情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或最好被冻结在琥珀中,这在神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我的结果是什么? 基督徒可以质疑任何事。 我们可以自由地对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有时,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 但通常情况下,对既定秩序持怀疑态度的基督徒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错过的东西。 多萝西·戴(Dorothy Day)、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康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都曾对一些现代思潮打上问号:自由主义、民主、人权、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核心家庭、数位科技、美国 帝国——无论哪一个,他们都曾将其置于被告席上,对其进行质疑。 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些人不再支持我们了。 但有时,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因此,“怀疑民主”也不应被诋毁为一种基督教民族主义。 至于我在最前面所形容的五种病态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我们有理由反对,也有理由为它们贴上其他贬义的标签,但“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不是最好的标签。
这并不是说“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过于强烈。 而是它太软弱了。 使徒保罗有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基督教民族主义”:“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而这个更改过的“假福音”在政治上的展现只是这种精神疾病的症状。 但这类福音确实以现在进行式出现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过,在我们振奋对抗假福音的同时也应受到责备:因为除了圣灵的大能,没有什么足以医治这样的假福音。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学副教授。 他着有四本书,包括《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and 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