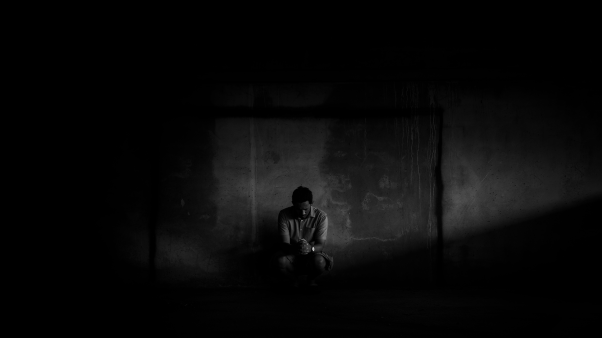2022年六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阳光明媚。芝加哥桥港(Bridgeport)新生命社区教会到附近的一个公园举行户外敬拜,也是这个教会英文堂和中文堂联合聚会。当天两个堂的两位牧师用茶聊对谈的方式讲道,会众则散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听道、祷告。讲道前带领大家唱诗敬拜的人当中,吉他弹得相当有水平的弟兄是崔宇,主要领唱的姐妹是小旭。
崔宇和小旭是“荆棘火”乐队——一个由一批年轻的基督徒中文圣诗创作者组成的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的属灵带领人是新生命社区教会中文堂的年轻牧师沙龙。
再早几个月,陈明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一个校园事工退修会中带领敬拜。他是基督使者协会(AFC)校园事工的全职同工,同时也是另一个圣诗创作团队的组织者。去年,在AFC的农庄退修中心举办的职青基督徒创意营会上,带领诗歌敬拜的人当中有位吉他手叫栾欣,他同样是既从事圣诗创作、又从事校园、职青事工的同工。
这几位年轻的中文圣诗创作者目前在华人基督徒当中还不太有名,他们创作的诗歌还没有像诸如“赞美之泉”、天韵合唱团和泥土音乐那样的创作团队的作品在华人教会中广泛地被用在敬拜赞美中。但是他们的诗歌创作跟校园或职青事工关系更密切,而且他们更愿意在新媒体上发布自己的作品——例如“荆棘火”会把一些他们新创作的一些作品录制出来放在他们的YouTube频道上。
华人教会爱唱的诗歌,一些是从优秀的英文诗歌翻译而来,一些是像“赞美之泉”等比较知名的中文诗歌创作团队的作品。我对这批年轻的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圣诗创作者充满好奇:他们为什么会认为需要创作新的中文圣诗?他们从事创作的动力跟他们委身的校园及职青事工有怎样的关系?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别人创作的中文诗歌,以及对提高自己创作的水平有什么想法?……
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沙龙、崔宇、小旭、陈明和栾欣等几位诗歌创作者,请他们分享个人的创作动机和感想。
请问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作中文诗歌?
沙龙:对我来说,想用中文创作新的诗歌诗歌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中文就是我们的母语。而我是蒙了上帝的呼召要来事奉一个主要由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和职青构成的华人教会。我们当然也会使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诗歌以及其他中文诗歌创作团队写的诗歌来敬拜,我们也为已有的中文诗歌感恩。但是我还是希望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自己创作新的诗歌。
用诗歌敬拜上帝本来就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像我们常说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就像呼吸一样必须,唱诗敬拜对基督徒来说也像吃饭、喝茶一样自然。我喜欢中国的美食和茶文化,也有一点做饭和泡茶的恩赐,所以很自然地,在我的服事中,我会自己动手为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做饭、泡茶。这是一种很接地气、也能够发挥自己恩赐的服事。创作诗歌也是如此。我信主以前就喜欢弹吉他、玩音乐,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现在回头看,感觉上帝都有预备。
陈明:老实说,我对自己创作中文诗歌没有太多把握。但是我自己是学音乐出身,有过音乐的专业训练;同时,我又受过基督教教育的装备,在我的神学理解当中,诗歌创作是非常好的一种个人敬拜神和反思信仰的操练与体现。作为一名传道人,我也认为这是我以创作为途径,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帮助大家反思和操练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服事。所以诗歌创作确实是我服事的一部分。
在你创作的过程中,你感觉最困难的难处是什么?
崔宇: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也许是寻找到介于服侍教会和自我表达之间的平衡吧。一个创作基督教音乐的人,自然希望用最好的词句来表达他内心最真实深刻的想法和感受。如果能找到知音,是很幸福的,但如果不能,他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初心,去表达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声音,只为了迎合周围的人的审美。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又的确不能放下服侍教会的心去做诗歌,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有的时候,我们的作品可能过于集中在自我表达,以致很难被会众理解。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可以被人听懂,可以带给人见证,可以带给人感动、鼓励、启发、安慰,最终可以帮助人们追随他们的信仰,与神更加亲近。如果我们写的诗歌仅仅想要自我表达、自我感动,而失去了群体敬拜的功能,它们仍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
小旭:创作出和歌词契合、并且好听不落俗套的曲子,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我不是学音乐的,对乐理和乐器的掌握有限。
陈明:我以前曾经是一名流行歌曲的词曲创作者,写曲子对我来讲并不是最难的,反而是作为诗歌信息主要载体——歌词部分的创作,是我认为最困难的地方。我心目中那种具有层次与深度的诗歌歌词,至今还未创作出来。
能否以你自己写的诗歌为例,分享你在创作中感受最深的经历?
小旭:我写的第一首诗歌叫作《新生命》,没有发表过。副歌是我在祷告时,连词和着旋律唱出来的。那天我是经过特别深的一个挣扎、陷在对自己非常失望和厌恶的情绪里,但是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我在祂眼里的样子,是一个已经被耶稣宝血更新了的人,是一个被圣灵主导的生命。
我就顺着我的感动,一边唱,一边把歌词在电脑上敲了下来。那首歌的创作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灵修和经历神的过程,让在祷告中我意识到神已经给了我新生命,所以我可以活出不再被罪拖累缠裹的生命来。纵然我还有软弱,神看我在祂里面仍然是“毫无瑕疵,全然美丽”,因为祂看到的不是我,是耶稣,而且祂是以发展、成长的眼光在看我。我真的感觉一下子就从试探和挣扎中被救拔出来了。
在团队合作创作中,你们怎样处理因为个人风格、偏好、意见等等的不同带来的冲突?
陈明:通常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歌词创作基本原则,譬如歌词在神学上的严谨、传递的信息要明确、要有福音性,等等。如果在涉及这些原则的问题上争论,以严肃、严谨的态度来把关,我认为是好的。但对这些原则之外的不同,我们需要保持忍耐和有弹性,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风格与音乐曲风的偏好。
栾欣:按理说基督徒应该操练彼此顺服,但做音乐这件事,很多时候是很难妥协的。比如在对编曲风格的意见差异太大的时候,是很难“彼此顺服”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反复修改,尽量做到不同偏好的队友都能满意。曾经有一首歌我们写过27个版本。
小旭:团队合作也有它的好处。当我自己想不出好的旋律时,我会和我们团的成员一起jam(即兴演奏和哼唱),寻找灵感,或者请团长崔宇帮忙操刀作曲。
常常有基督徒批评一些现代中文圣诗“听起来像流行歌曲”,你们怎么看? 你们如何看待诗歌创作中的传统与创新?你们是如何改进自己的诗歌创作的?
崔宇:我其实鼓励自己带着开放和欣赏的心,去看待当今各种中文诗歌,即使它们很多听起来和流行音乐很像。我不轻易否定它们。我觉得,这些听起来像流行歌曲的诗歌,很可能是很多年轻及初信的基督徒在敬拜中成长的必要过程。这些流行歌曲可以用他们能够最快接受的语言,来鼓励他们的信仰。 。
曾经有属灵长辈和我们分享说,跨代际服侍,本质上也是一种跨文化宣教。它要求你要用年轻一代熟悉的文化和语言,去服侍他们。如果你强行用你自己熟悉的文化和语言服侍他们,就会制造出“跨文化”的障碍。
当然,我们也不能单单停留在这种类型的中文诗歌中。敬拜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应当是丰富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是丰富的。我们需要让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尽可能地把这种丰富表达出来。音乐和诗歌是可以提供语言所不能提供的感染力的。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也需要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富有深刻内涵的中文诗歌。
陈明:我觉得需要把歌词和曲调分开来看待。从歌词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在华人教会流行的一些中文诗歌歌词确实比较单调重复、像是在套公式,而且神学用词不够严谨。
但从曲调上来看,历史上的圣诗有不少是使用那个时代通俗歌曲的旋律,重新填词成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旋律,大都拥有好记、易学易唱的特点。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歌词在圣诗中的角色是主要的,歌词的创作需要慎之又慎,甚至应当将歌词创作看做预备一篇需要字字精雕细琢的讲道。
栾欣:很多现代中文圣诗其实并不“像流行歌曲”。它们的问题是音乐风格单一乏味,曲调难听,音乐水准比同时代的流行歌曲落后。很多不信主的人也会哼两句《奇异恩典》或是《普世欢腾》,那是因为当年的基督徒把诗歌做到了高水准,才能流行。所以我的盼望是:今天基督徒制作出的诗歌,音乐水准足以与同时代的流行音乐匹敌。
这需要既有创新,也有对传统的继承。我自己会尝试不同的现代音乐的风格——可能第一首硬摇滚风格的中文诗歌和第一首金属风格的中文诗歌都是我制作的。但我们写的歌词,跟以前的那些经典圣诗一样,是在讲述一个古旧的福音,这是继承传统。
沙龙:继承传统不等于就是照搬西方的基督教音乐。我们既然是用中文写歌词,也应该写出中文独有的美和韵味。我自己尝试过采用一些类似唐诗宋词的比较古雅的风格写词,我觉得现代的歌词可以通俗易懂,也可以有一些阳春白雪,有一点文学上的美感的追求。
提高作曲的品质,需要加强专业性。我们做创作一段时间后,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在音乐方面的不足。我前段时间专门去认识了一些经验丰富、专业从事音乐制作的高手,请教他们,也请他们帮忙为我们创作的歌曲配乐、润色、录制,做一些专业的处理,也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培训。既然我们是有呼召来做,就要做得专业,尽量做出精品,不光是歌词要好,音乐也要好,专业性也是呼召的一部分。